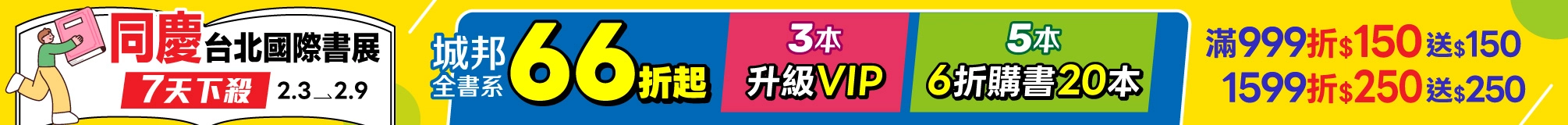分類排行
-
經典古文小寓言:讀動物故事、打造文言文基礎、閱讀素養題全部學起來!(高詩佳老師作品)
-
經典古文小寓言2:走進奇花異果花園,文言文基礎 × 閱讀素養,一起升級!
-
小翻頁大發現:我的環遊世界大發現【暢銷紀念版】(超值附贈─100×70cm 超大幅世界地圖海報)‧核心素養學習最佳讀物
-
野花甜米露:白有娟的森林動物點心饗宴【SDGs主題繪本×社會情緒×人際互動】提升兒童情緒智商和情感療癒力,和動物朋友一起啜飲飽含深情的飲品吧!
-
荷葉煎餅:白有娟的森林動物點心饗宴【SDGs主題繪本×社會情緒×人際互動】提升兒童情緒智商和情感療癒力,來一場特別的夏日慶典吧!
-
山茶花包子:白有娟的森林動物點心饗宴【SDGs主題繪本×社會情緒×人際互動】提升兒童情緒智商和情感療癒力,和動物朋友們一起做香甜的山茶花包子吧!
-
【環境教育繪本】地球請你幫幫忙!玻璃、紙類、金屬、廚餘……回收物的再生之旅(符合108課綱.SDGs永續閱讀書單.地球小公民必讀繪本)
-
媽媽,為什麼要快一點?(時間觀念+親子關係+共讀繪本)
-
校外教學到火山(國際十一項大獎肯定《校外教學到月球》、金鴨子圖畫書獎《校外教學到海底》系列作)
-
雞蛋的祕密
最近瀏覽商品
內容簡介
韓國總統文在寅親筆寫信致謝作者!
臺灣社會的警惕之書!
「要知曉一個社會的靈魂,就看他們對待孩子的方式。」
.因為「你是我生的」,所以打小孩是正當管教,不是虐待?
.「經紀人媽媽」和「大雁爸爸」們,渴望以孩子的成就證明自己人生。
.在課堂上要求多元文化家庭的孩子舉手,反被貼上「不一樣」的標籤?
.少女未婚懷孕,誰陪她面對學業中斷、墮胎或生下孩子的人生抉擇?
.低生育率的形成,難道是因為現代女性高學歷、眼光太高?
我們對孩子的「愛」,會不會是以「正常」為名的「異常」?
本書重新剖析一般人眼中,由父母與子女組成的所謂「正常」家庭,以及亞洲社會最重視的傳統家庭觀,看見家庭內隱形的權力如何壓迫、影響孩子的權益與成長,提醒我們──單由一方所建立的關係,實際上是一種暴力。
作者金熹暻以多年在兒童人權組織工作的經驗,寫下所謂「正常」家庭型態以外的家庭,在社會上遭受的歧視;以及當家庭內的暗影蔓延到職場、學校、社會時可能產生的悲劇。
究竟是誰定義了「正常」與「異常」?父母與家庭、社會與國家又該做出什麼改變?本書試圖提出消弭偏見、扭轉觀念的解決之道。
獲獎記錄
◆ 2018入選韓國年度好書
◆ 2018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優秀圖書社會科學類
◆ 2017《國民日報》、《韓民族日報》今年之書!
◆ 《朝鮮日報》、《東亞日報》、《京鄉新聞》推薦好書
名人推薦語
專文推薦──
白麗芳(兒童福利聯盟執行長)
莊喬汝(律師)
共鳴好評──
金鉉京(人類學家)
陳俊朗(「孩子的書屋」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張淑惠(「歐巴桑聯盟」總召)
番紅花(作家)
鄭惠信(精神健康醫學科醫師)
劉宗瑀(小劉醫師)(阮綜合醫院乳房醫學中心主治醫師)
(依首字筆畫排序)
======================
面對少子化、兒虐、殺子自殺等問題,臺灣和韓國一樣面臨相當大的挑戰。該有更多成人閱讀此書,為社會帶來更多反思與改變,給孩子一個更好的世界。──白麗芳(兒童福利聯盟執行長)
生動展現大人如何以「家庭」為名踐踏兒童人權,也論證出:何以不能只將家庭問題推卸給家庭,深具說服力。──金鉉京(人類學家)
本書透過不同國家的經驗,回頭對照反思臺灣在家庭福利、兒少保護政策、親職論述等走到了什麼位置、還有哪些地方需要努力。──莊喬汝(律師)
少見以孩子為中心談論家庭議題的書,針對各種類型的暴力檢視家庭問題,寫得平實而深入,是一本難得的好書。──陳俊朗(「孩子的書屋」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身為推動不打罵教育的團體成員及政治參與者,本書讓我如獲至寶!推薦給每一位會遇見孩子的你,一起努力讓臺灣成為重視兒童人權、不再有兒虐的國家。──張淑惠(「歐巴桑聯盟」總召)
單憑一方所建立的關係,實際上是一種暴力。金熹暻快速精準的直指問題核心。──鄭惠信(精神健康醫學科醫師)
明明應該珍愛孩子,為何虐待、暴力事件頻仍?教養與虐待之間,背後的權力界線該如何客觀察覺?藉由此書分析來對照臺灣現況,不勝唏噓!──劉宗瑀(小劉醫師)(阮綜合醫院乳房醫學中心主治醫師)
目錄
前言 渺小的個人,巨大的權利
第一章 家庭是一道護城牆?家庭內,子女是我的所有物
「你是我的」──親密的暴力和體罰
對待孩子的態度,即為社會的樣貌
過度保護或疏忽,源自將子女視為所有物
家人「結伴自殺」的不可能性
親權不是權力
第二章 韓國的「不正常家庭」:家庭外,唯有「正常」才是自己人
為什麼只有未婚媽媽,沒有未婚爸爸?
收養,被輸出到「正常家庭」的孩子
在韓國,有色人種家庭代表的意義
第三章 誰定義了正常和不正常家庭?被塑造的信念──能信任的只有家人
在韓國,家庭何以變得如此重要?
以家庭為單位,階級向上流動的社會
何以家庭主義會擴散到職場、學校和社會?
第四章 當家庭問題層出不窮──為了共生共存,我們該怎麼做?
父母體罰禁止法如何改變社會?
生活回歸個人,解決問題要靠集體
共同生活,將家庭的包袱交給社會
結語 勾勒出自主的個人與開放的共同體
附錄 延伸推薦書單
關於成為人、人權與童年期
關於近代化、家庭問題
關於歧視、共感與同理心
內文試閱
「你是我的」:親密的暴力和體罰
二○一四年春天,在蔚山與漆谷發生兒童受虐致死事件,輿論一陣沸騰,旋即又發生世越號慘案,孩子之死沉重的籠罩全國之際,國會針對「政府的兒童虐待預防對策」召開研討會。我看著會議進行,而就在法務部的討論者發言結束,正要跳到下個階段時,討論者補充了這段話。
「啊,還有,最後希望專家可以幫忙定義一下虐待與體罰的界線。因為在和檢察官聊天時,他們經常提到『大部分父母在養育孩子時,偶爾都會打個一、兩次,而我自己也是這樣。要先畫分出體罰的範圍在哪,從哪裡開始又是虐待,法律才有辦法因應,不是嗎?」
在差不多的時機點,我和在《中央日報》社會部擔任記者的後輩一塊吃午餐,接著聊到二○一三年開始,在蔚山、漆谷連續發生的兒童受虐致死事件。我們一同聲討虐待有多殘忍,然後討論到NGO可以和媒體聯手舉辦活動。我向後輩提議,不如舉辦全面禁止體罰的活動。當時我正在整理蔚山兒童受虐致死事件的調查結果,深刻感受到有需要改變父母對體罰的基本認知。
可是,後輩的反應卻很不以為然:「體罰?哎呀,我也打過孩子,那和虐待有段距離吧?我們不談那種輕微的狀況,舉辦以虐待為主題的活動啦。」
我聽著監察官與記者表示可以不把體罰當成一回事,領悟到許多善良的人很輕易就把正常與不正常區隔開。他們認為在「正常家庭」內允許的體罰,以及在「不正常家庭」發生的虐待截然不同,絕對不會混淆,就像正常與不正常一樣天差地遠。
這種多數人擁有的觀念有點奇怪,我們不妨用女性遭受的暴力來思考好了。近年來,我們不會認為「性暴力雖然不對,但夫妻或男女朋友爭吵時,打個幾巴掌也是難免的」,很久之前,大家就已不再將性騷擾看成是為了拉近職場關係所開的玩笑,而會將其納入性暴力的範疇,並加以禁止。即便在現實生活中,性騷擾依然層出不窮,但大家也不會說:「大部分公司都是這樣,無傷大雅啦。」可見社會認知有了很大的進展。
但面對孩子時就不同了。雖然大家認為虐待是不對的,但養育孩子時很難不打孩子。大家都說:「這是為了糾正孩子的壞習慣,不得不動用體罰。」「我自己也是被打大的,還不是長得好好的?」許多人就像前面舉例的檢察官與記者,認為孩子的體罰和虐待存在距離,壁壘分明。果真是如此嗎?為何我們會有這種想法呢?
想必沒有人會反對「兒童虐待不該存在」這句話。每次爆發可怕的虐童事件時,我們憤怒的想:「怎能戴著人類的面具,幹出那種事來?」將虐待孩子之人視為不正常的惡魔而咬牙切齒。
另一方面,根據國家人權委員會《二○一六年國民人權意識調查》,有大約一半的國民依然認為可以體罰兒童與青少年。我敢肯定,在此調查中贊成體罰的一半國民幾乎都反對虐待,但之所以會頻繁出現要明確定義體罰與虐待的主張,原因也在此。可是允許體罰的態度,以及虐待之間的距離究竟有多遠?兩者真能徹底切割開來嗎?
我還記得二○一五年末,一名十一歲小女孩為了逃避父母監禁與虐待,攀爬瓦斯管線逃家的事件。根據當時的報導,小女孩並非初次脫逃,之前也曾經為了躲避家暴與飢餓,好不容易才逃出家外,卻被路人發現,將她送回家裡。第二次攀爬瓦斯管線逃出時,又因超市老闆報警而被發現。警察詢問她家住哪裡時,她則謊稱自己是「從社福機構跑出來的」,只因為害怕會再次被送回家。
我們經常會責怪這是一個鄰居冷漠無情的社會,但若是路人還會主動將模樣悽慘的小女孩送回家,就表示大家並沒有對少女的處境漠不關心。與其說是漠不關心,會不會是認為父母打孩子的行為「在所難免」,所以才帶少女回家呢?
再來看看二○一三年令大眾瞠目結舌的漆谷兒童受虐致死事件吧。儘管在孩子身亡的一個月前,舅舅看到了孩子們身上的瘀青後報警,警察也出動了,生父卻辯稱「是用雨傘阻止姊妹吵架時失手造成」。警察在父親的面前向孩子求證真偽,看到孩子點點頭後便撤退了。那孩子先前曾向派出所舉報繼母施暴,但父親接受調查時卻推翻了口供。在孩子身亡之前,學校、警察、民間團體、兒童保護機構、鄰居等透過各種管道得知虐待事實的大人總共有三十七名,卻沒有一個人避免孩子不幸死亡。揹負殺害妹妹罪名的姊姊,直到遠離擁有監護權與養育權的父親,並接受心理治療之後,才一五一十道出繼母的施暴行徑。
當大家和整個社會皆認為,父母或養育者體罰孩子在所難免時,對於虐待的敏感度也會降低。在社會彌漫著允許體罰的氣氛之下,會有根除兒童虐待的方法嗎?我敢斷言沒有。在有大約一半社會成員接受可以對特定年齡層、在特定條件下使用暴力的社會裡,被視為無關痛癢的體罰會如同毒菇般,茁壯為更趨嚴重的暴力,沒有任何遏止的方法。
體罰與虐待之間的距離
就加害者的實際行動來看,就會發現體罰和虐待的距離並不遠。二○一四年秋天,在蔚山發生七歲小女孩哀求想去郊遊,結果慘遭繼母凌虐致死的事件。雖然之後也發生許多類似事件,但這個案例的嚴重性在於,即便在幼兒園老師檢舉、兒童保護機構介入之後,依然無法挽回小女孩的性命。政府應該要著手調查,防止虐待的保護體系究竟是哪裡出現了漏洞,才會無法阻止孩子的死亡,並加以防範才是,但不管是現在或當時,除了警方搜查,政府都不曾調查或分析兒童保護體系是否做了適當的處理。
民間團體和專家認為無法對政府不周全的因應措施坐視不管,於是有志一同的決心親自調查,組成「蔚山兒童受虐致死事件真相調查暨制度改善委員會」。由當時民主黨南仁順委員擔任委員長,國會與民間共同調查事件,並出版了記錄其結果的《李書賢報告書》,而我則擔任委員會祕書長,負責在當地調查與撰寫報告。在調查事件的過程中,有一項議題令我深刻感受到,如果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不管兒童保護體系再完善,虐待也不會就此消失。這項議題即是體罰。
幼兒園老師發現虐待的狀況後,進而向兒童保護機構檢舉。老師告訴社工,小女孩的繼母與親父恰如典型的虐待加害者,表現出極為高壓且防禦的行為模式。某天,小女孩的生父致電給社工,如此爭辯:「孩子是由奶奶拉拔長大的,所以很沒規矩,性格自由奔放。因為行為上有嚴重問題,才不得不出手打她。你養過孩子嗎?看看其他家的孩子也知道,有哪家的孩子不是這樣長大的?」生父還勃然大怒:「家庭(離婚後孩子由奶奶撫養,直到生父再婚後,又將孩子帶回自家管教)好不容易才上了軌道,但因為兒童保護機構介入,整個都被打亂了。」
為了教孩子守規矩才打孩子的主張,難道是為了掩飾之後演變成打斷肋骨的「蓄意」虐待,才說出的謊嗎?我不這麼認為。根據多位社工的說法,沒有任何虐待孩子的父母或監護人,起初是帶著想致孩子於死地或傷害孩子的「意圖」。書賢的狀況也是從一、兩次的體罰,慢慢變本加厲,最後才演變為肋骨斷裂,骨頭插入肺中,最後出血過多導致死亡的地步。
為了管教孩子才打孩子的主張,成為最折磨社工的辯解。「我的孩子我會自己教,少來多管閒事。」每當社工接到檢舉,前往現場進行調查,就會碰到不計其數拒絕諮商與調查的情況。即便接到有人檢舉虐待,也有很多警察認為:「父母總有這點權利吧?」而不以為意,沒有確實進行調查。
可是,藉由過去眾多分析與研究可知,世界上大部分的虐童事件均是一般人偶發性的體罰失控造成的結果,而非極度不正常的人蓄意行使的暴力。
向成人暴力說NO,孩童暴力卻OK?
就像大家將兒童虐待與體罰分開看一樣,大家也經常將孩童暴力與成人暴力區分開來。根據二○一六年,京畿道家庭女性研究院以一千五百位當地民眾為對象所進行的「暴力允許態度」調查,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成人認為「毆打並威脅對方的行為即為暴力」,可是在親子關係中就不同了。同意「為糾正子女的習慣,父母可以毆打、威脅子女」的比例為百分之四十八.七;同意「為教導子女禮儀,可以威脅孩子說要打他」的比例為百分之三十五.三;同意「指導孩子學習時,可以威脅孩子說要打他」的比例則為百分之二十三.三。
由此可見,父母可視情況對子女施暴的思考方式依然根深蒂固。這是因為父母將子女視為所有物,因此只要父母認為有必要,就可以對他們行使暴力。即便體罰儼然是一種對於人格主體的毆打與暴行,卻仍然存在於成人、父母的觀點之中。任何人都不會以愛為由,或為了糾正他人而出手,只有孩子,成了唯一能以管教之名毆打的群體。
支持體罰者主張:「就算是必須毆打不成熟的孩子,也要教導他們。」長期以來的論調一直如此,若是為了糾正比自己弱勢、低等之人,暴力就可以正當化。然而,有無數研究指責,體罰非但毫無教育效果,反倒會使暴力內化(internalization),造成人格扭曲,也只會引起孩子的恐懼,不會促使他們反省。
「內心受創、恐懼、傷心、膽怯、孤單、悲傷、生氣、感覺被拋棄、被忽視、發火、厭惡、恐怖、丟臉、悲慘、受到打擊。」這是二○○一年英國救助兒童會根據孩子挨打的經驗所整理出來,孩子們對於「體罰」的記憶。儘管孩子使用了超過四十個形容詞表達對體罰的可怕感受,但沒有一個孩子說出感到抱歉或反省的字眼,這表示體罰不僅在教育上成效不彰,而且只會在情緒上對孩子造成莫大傷害。
「因為父母的管教式體罰意圖為善,所以不會侵害身體的健全性和身為人類的尊嚴。」這僅是從父母、成人的角度分析的主張,人類學者金鉉京就曾在《人,場所,環帶》一書中,針對「體罰教導孩子什麼?」做出以下分析。
「體罰的理由百百種,上頭依附著各式各樣的訓誡,但當跳脫表面的那些說法,體罰始終反覆傳達出一個訊息:體罰隨時會故態復萌。你的身體完全不屬於你,而我隨時都能對你動手。一旦同意體罰,就代表接受這樣的教育方式,同時也接受了羞辱的悖論。羞辱不僅是否定他人的人格,還強迫對方必須同意這件事。在遭受羞辱之人同意的瞬間,羞辱不再只是羞辱,而是儀式的一部分、秩序的一部分。最後,羞辱成為以否定自身本質為最終目標的暴力。」
「我隨時都能對你動手」的教育方式,和過去對女性施暴蘊含著相同的訊息。包含體罰在內,在親密關係中對他人反覆施暴的行為,都傳達出相同訊息:我隨時都可以控制你的權威主義思想。能夠決定你存在的權力不在於你,而是在毆打你的我身上,以及用蠻力使對方閉嘴、否定對方的話語,並試圖將自己的思想灌輸給對方。
「唯有用藤條打孩子,用嚴厲嚇人的方式管束,孩子才不會出現問題行為,乖乖長大。」這樣的普遍觀念並沒有任何科學根據,反倒有數不清的數據顯示出相反結果。體罰能帶來正面效果,只不過是大家如此相信而已,顯示體罰具有負面影響的研究早已屢見不鮮,這也稱不上是爭論。
母親的藤條,或是「愛之鞭」
生長在將體罰視為管教方式,而且使用得比現今更廣泛的年代,不知既成世代(指已經在社會具有一定地位、掌握大部分資源的上一代。)是否太沉浸於過去,才導致他們通常都有把父母的體罰美化的傾向。不僅是個人之間的對話,就連公共溝通亦是如此。
一旦說起要禁止父母體罰,就會有人提出異議:「我也是被打大的啊。」這裡預設了一個前提:因為從小被打到大,也就是在父母持鞭嚴厲教導下,自己才能順利長大成人。其中可能也包含了一種不快的心理,認為這是在攻擊父母用藤條打孩子小腿的行為是錯誤的。
雖然有很多人會說「愛之鞭」是韓國父母傳統的教育方式,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在其他包庇父母體罰行為的國家中,也經常使用「愛之鞭」(cane of love)的說法,因此這種嚴厲、賺人熱淚的愛之表現並非韓國父母獨有。「愛之鞭」的說法,意味著根據毆打者的意圖,某些暴力能夠正當化,但這些全是持鞭者的論調,對於挨打的孩子而言,無論體罰的原因是愛或憤怒,根本毫無分別。
「多虧了體罰,今日我才能成材」的論調,不僅存在於韓國,也存在於其他國家,每當禁止體罰成為社會議題,就會出現此種擁護論調。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在《羅素短論集》(Mortals and Others》寫道:「曾經在學生時代被藤條或鞭子打過的人,幾乎都相信自己是因此才成為更好的人。在我看來,這種信念本身即是體罰造成的負面影響之一。」
倘若兒時沒有被藤條打,我會變成什麼樣的人呢?因為沒有親身經歷過,所以無從得知,也許會和現在差不多,或者成為對暴力擁有高敏感度、一個更好的人吧?
既成世代在那個年代限定的文化環境中教導子女,可是,不能因為自己生長於何種環境,就主張該方法迄今依然有效。研究體罰弊病的發展心理學者伊莉莎白.格爾沙霍夫曾用汽車安全帶的比喻說明。有相當多的成人在沒有汽車安全帶的時代長大,但沒有人會說,多虧了這件事我才能順利長大。應該說,即便沒有安全帶,人也可以平安無事的長大。相同的,我們也不能說多虧了父母的體罰,我才成為一個不錯的人,而是:「即便遭受父母體罰,我依然成了一個不錯的人。」
「我做了該打的事」
姑且先不論體罰既不具有管教效果,且對孩子有害,我之所以認為體罰是一種問題,更大的原因在於這會導致孩子將加害者的論點內化,認為暴力也是一種愛。
若是在我深知對方很愛我,或者非常依賴我的狀態下,對方對我拳腳相向的話,這不僅是一種身體傷害,更是踐踏對方心靈的一種惡質暴力。多數的家暴和約會暴力均屬此類。二○一五年,Twitter上很熱門的約會暴力證詞便是如此。加害者把「妳做了該打的事」當成施暴理由,將過錯推到被害者身上。「害怕失去對方勝過於挨揍」的被害者則責怪自己老是做了該打的事,下定決心要成為更好的戀人。
我在調查蔚山兒童受虐致死事件時,也聽到與此極為相似的故事。根據當時社區鄰居、教師和社工的證詞,加害者和孩子的關係和Twitter上看到的約會暴力加害者、被害者的關係相似。
即便在不為人知的暴行曝光後,加害者仍怪罪到孩子頭上,表示是孩子說了謊,做了該打的事。另一方面,即使這個孩子被打得頭破血流,卻仍以「很會做菜的漂亮媽媽」為題寫了一首詩,還畫了圖,努力想討好加害者。倘若約會暴力的受害者是因為害怕失去戀人,將加害者的話語內化,那麼在虐待中犧牲的孩子則是為了存活,才將加害者的論調加以內化。儘管成人與孩子面臨的處境不同,被害者對於加害者的依附心理,是在披著愛的外皮所行使的暴力中都會看到的悲涼樣貌。因為,加害者總會在施暴後,反覆訴說「往後一定會好好待你」。
以「愛之鞭」為名連結暴力和愛是非常危險的,這無疑是教導孩子,只要愛著對方,身體上占有優勢者便可用蠻力壓制他人。即便在愛與照顧的關係中,力氣強大或是擁有權力者,均可用暴力來解決問題。體罰教導孩子,「為了獲得你想要的東西,打人也無所謂」「攻擊他人也沒關係」。
在親密關係中,約會暴力、體罰等以愛為名所行使的暴力,在無形之中強迫被害人相信,「是我做了該打的事」。為了能夠活下來,於是挨打者必須貶低、否定自己,認為問題是出在自己身上。
但世界上哪有什麼「該打的事」?這種醜陋的暴力所留下的傷痕,在我所聽到的故事中最令人於心不忍的,莫過於二○一四年一位住在社福機構的孩子。他來到社福機構前,經常被父母體罰,而在輔導過程之中,當他聽到「我的身體很珍貴」這句話時,他如此說道:「書上是這樣說,可是我不懂,為什麼我的身體很珍貴,每天被打很可憐,有什麼好珍貴的……」令人遺憾的是,這個孩子在機構內也身陷對其他孩子性騷擾的風波。要是不曾被好好對待,就不會認為自己和他人同樣都很珍貴。
愛與暴力
將愛與暴力連結在一起的思考方式,蔓延到社會的每個角落。不僅僅是體罰,上述的約會暴力、家庭暴力是如此,而每到大學入學季,新生歡迎會以體罰建立新生紀律的扭曲模式亦是如此。使用暴力的行為,究竟為什麼會成為一種表達「歡迎」的方式呢?我認為,使大家「變得能夠接納暴力」的首要次文化,即為父母的體罰。
根據人類學者的研究,社會階級化、政治決策非民主性、暴力文化越嚴重的社會,體罰現象也越嚴重。「即便父母表示自己不具有該意圖,體罰仍十足展現了父母與子女間『力』的差異。體認到這其中不平等的孩子,即便長大成人後,也很容易把伴隨力量與權力而來的不平等視為理所當然。」根據觀察,相較之下,日常生活中較常出現對孩子體罰的地區,也會出現對太太或兄弟姊妹過度施暴的現象。
心理學家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人類的善良本性──為何暴力會衰退?》(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一書中檢視暴力性的歷史,並以美國為例,說明體罰的贊成率和殺人率的軌跡相符。容許體罰的次文化也意味著助長成人的極端暴力。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之所以強調杜絕體罰是「減少並防止社會上各種暴力的核心策略」,原因就在於此。
隱蔽暴力的一般觀念在過去也屢見不鮮。就在不久前,大家還能若無其事的大聲嚷嚷「明太魚乾和女人,每三天就要打一次」這種駭人的話。如今韓國社會至少不會以愛為名,試圖隱蔽對女性的暴力行為,但唯有面對孩子又是另一碼子事。我們的孩子就生活在被美化為愛與管教、容許暴力的最後殖民地上。
在電影《驚爆焦點》(Spotlight)中,為揭開天主教神父對兒童的性暴力而奮鬥的人權律師說道:「養育一個孩子要靠整個村子,虐待一個孩子亦同。」
儘管這句話是為了強調全村的沉默與幫助等同共犯,但我認為這句話也適用於我們的社會。正如同父母無法獨自撫養孩子,父母也無法獨自虐待孩子。小看並容許體罰的態度、寬待暴力的情緒、無公權力的介入等,使得漏洞頻出,最終導致在某處的孩子受虐致死。就此層面來看,將子女視為父母的所有物、寬容父母體罰的韓國社會,不也加入了全村虐待孩子的行列?
作者資料
金熹暻(김희경)
金熹暻(김희경) 首爾大學人類學系畢業,曾任社會、文化線記者長達18年,看見許多社會的歧視或漠視導致兒童權益受損,甚至發生悲劇。因此加入國際兒童救護組織,致力於改善制度與認知的「權利宣導(advocacy)」。之後進入政府部門,現為女性家族部副部長。 其所著《異常的正常家庭》榮獲2018年度好書、文化體育觀光部「社會科學類優秀圖書」,也入選《國民日報》、《韓民族日報》、《朝鮮日報》、《東亞日報》、《京鄉新聞》等多家媒體之推薦好書。更收到韓國總統文在寅的親筆致謝,為韓國社會的兒童權益問題敲響警鐘。 其他著作有《賣座電影的再構》、《女性的工作:重新整理》(合著)等;譯作有《Asian,English》、《藍眼、褐眼》等。 經歷 《東亞日報》記者 「Save the Children」權利宣導部長、本部長 「人權政策研究所」理事 「移居背景青少年支援團體」理事 文化體育部部長助理 女性家族部副部長
注意事項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