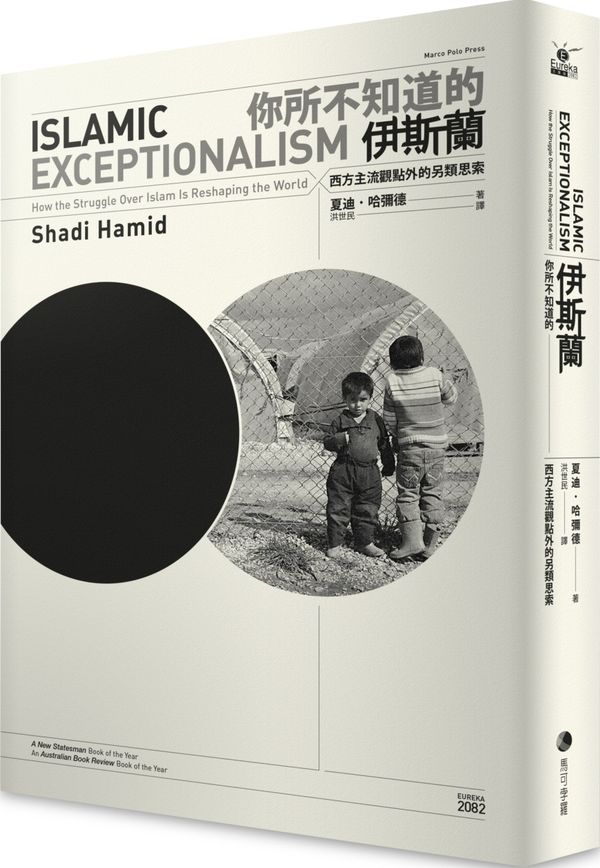分類排行
內容簡介
★伊斯蘭研究專家、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林長寬審訂、導讀
★《新政治家》(A New Statesman)年度選書
★《澳大利亞書評》(Australian Book Review)年度選書
★《科克斯書評》、《華盛頓郵報》、《出版商週刊》一致推薦
了解當代中東政治動盪的必讀作品,破除世人對伊斯蘭世界的有色眼光
什麼是「伊斯蘭特殊論」(Islamic Exceptionalism)?
政治與宗教密不可分的伊斯蘭,是否發展出有別於西方的特殊性?
在時下保守、孤立主義日益興起的時代,我們該如何看待伊斯蘭世界?
當我們用譴責的眼光評斷「伊斯蘭國」等極端暴力組織時,
是否帶著西方中心視角的「傲慢與偏見」,而忽視伊斯蘭內在的發展理路?
本書作者夏迪.哈彌德是位埃及裔美國籍中東政治研究學者,在本書中,哈米德試圖呈現伊斯蘭主義運動的多元面貌,破除世人將「伊斯蘭」等同於「暴力」的刻板印象。此外,作者也希望傳達伊斯蘭世界在傳統上就與西方世界(特別指基督教世界)有不同的發展理路,我們不應該以「自由民主」的發展路線來框架伊斯蘭世界,而該把伊斯蘭放在「特殊的位置」上來看待。本書有助我們充分了解伊斯蘭的過往與現在,以及它在現代政治所扮演的吃重角色。我們不必喜歡它,但我們必須了解它——因為既是宗教也是思想的伊斯蘭,未來數十年仍將是一股不僅形塑中東,更撼動整個西方世界的力量。
目錄
導讀 「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或「伊斯蘭政治」(Islamic Politics)?(林長寬)
第一章 以屠殺為樂
第二章 伊斯蘭是「特例」嗎?
第三章 伊斯蘭的宗教改革
第四章 穆斯林兄弟會:從改革到革命
第五章 土耳其模式:掌權的伊斯蘭主義者
第六章 突尼西亞:在信仰上讓步的伊斯蘭主義者
第七章 伊斯蘭國:國家失靈之後
第八章 伊斯蘭、自由主義與國家:出口?
誌謝
註釋
導讀
「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或「伊斯蘭政治」(Islamic Politics)?
◎文/林長寬(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埃及裔的美國中東政治研究學者夏迪.哈彌德(Shadi Hamid)其新作Islamic Exceptionalism: How the Struggle over Islam Is Reshaping the World乃是歐美新生代研究者對傳統西方伊斯蘭運動之研究重新提出了較中立客觀的檢討,以及詮釋解析伊斯蘭運動對整個中東區域發展所扮演的角色。本書的標題取得相當中肯,Islamic Exceptionalism乃對應一般所謂的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國的特殊、優越性)的用詞。的確,相較於基督宗教或其他世界宗教,伊斯蘭有其特殊性與優異性;伊斯蘭本質或體制並非如一般刻板印象的認知:是落伍的,且與暴力脫離不了關係。
哈彌德這本書探討了「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或「伊斯蘭政治」(Islamic Politics)的意義與其實踐應用。宗教信仰與政治活動的關係一向是伊斯蘭文明體制結構的核心,因為伊斯蘭文明建立在伊斯蘭教義的基礎上,而文明發展的推手乃是穆斯林統治者。傳統的伊斯蘭政體即是信仰引導政治體制的建構,以及穆斯林社群律法的制訂與執行皆以伊斯蘭教義為基準,這種體制規範全以所謂的「神聖經典」——《古蘭經》、先知穆罕默德行誼(Sunnah)為依歸。這也是西元七世紀時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島提倡宗教、社會改革的必然結果。先知歸真後,穆斯林社群所締造的國家體制承繼了先知的教化(teachings),採取全然的政教合一制度,即所謂的「哈里發體制」(Caliphate),此體制以伊斯蘭法為基礎去運作落實真主阿拉(Allah)的旨意,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當伊斯蘭國家受到歐洲帝國殖民勢力的入侵與民族主義的引入之後方被廢除。
中東地區的順尼(Sunni)(編按:坊間或譯為遜尼)伊斯蘭國家在歐洲殖民勢力退出後,建立了民族國家,並對傳統古典伊斯蘭體制遺緒提出了檢討;大部分阿拉伯國家的發展朝向政教分離的世俗化體制,並以軍事強權獨裁掌控國家權力。此發展路線對於傳統伊斯蘭主義者(Islamist)而言,有如對文化認同與信仰價值的扼殺,因而激發了各式各樣的伊斯蘭運動(Harakat Islamiyyah, Islamic Movements)。作者列舉了幾個國家如埃及、土耳其、突尼西亞、「伊斯蘭國」(ISIS)深入分析、詮釋當代伊斯蘭主義運動的內涵與其不同層面的運作。而作者也檢視了歷史上伊斯蘭哈里發政權、體制的本質,即一般中文書籍常不當翻譯的「哈里發國」。所謂的Caliphate即是以哈里發(Khalifah, Caliph)為國家領導者之政體的稱呼,亦即在先知之後其繼承者(Khalifah)的門徒們所建立的「正統哈里發」(the Rightly Guided Caliph, Khulafa’ al-Rashidin)體制,意謂他們繼承了先知在麥地那所建立的政治與宗教合一政權,並嚴格遵守伊斯蘭法(Shari‘ah)的執行。之後,Caliphate一直被順尼穆斯林認知為國家當然體制。
雖然歐斯曼帝國(the Osmanlis, 1281-1924 AD)(編按:坊間或譯為奧斯曼帝國)在十九世紀初啟動了科技、經濟的現代化(歐洲化),但政治上仍維持著哈里發制度,一直到二十世初紀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革命成功後哈里發體制方被廢除,國家朝向全然的歐洲化與世俗化發展,伊斯蘭儀式被貶到私人生活空間,伊斯蘭律法與伊斯蘭經學院(Madrasah)亦被廢除。號稱中東第一個民主式國家(其實不然)的土耳其共和國在凱末爾的世俗化主義實行了五十年之後,幾乎將歐斯曼帝國的伊斯蘭文化遺緒掃空,人民的伊斯蘭認同與價值觀產生極大危機。一九七○年代起,凱末爾主義(Kemalism)開始受到檢討,而被認定失敗。隨之而來的是,普羅大眾開始反省「土耳其文化」的真諦,理解到歐斯曼帝國的遺緒與伊斯蘭價值觀無法全然拋棄,而逐漸有「伊斯蘭復興」思潮的醞釀發展,其中宗教分子不斷地思索如何恢復「歐斯曼伊斯蘭」的光榮,帶有伊斯蘭性質的政黨也因而產生,進入所謂世俗化體制內去挑戰「凱末爾主義」。「伊斯蘭意識」(Islamic awareness)開始茁壯發展,伊斯蘭主義分子不僅進入國會掌控政權,更試圖藉政策推行「再伊斯蘭化」運動,而且相當見效。然而,伊斯蘭主義分子掌權後卻在民主與獨裁之間擺盪,現今的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出身於右派伊斯蘭復興團體,在掌控大權後試圖以中央集權來落實保守伊斯蘭主義理念,其個人的野心造成了另一波極端主義統治者對溫和伊斯蘭主義者或世俗化主義者的迫害。艾爾多安無可否認地想建構現代哈里發制度,將總統職位轉成具「蘇丹」(Sultan)實質意涵的權位。如此激進伊斯蘭主義者的運作卻引發當前土耳其國家政治的動亂不安。
曾經是歐斯曼帝國領地的埃及在脫離歐斯曼帝國後,受到英國控管一段時間,也開啟了阿拉伯國家歐化之先驅。早在歐斯曼帝國末期哈里發政權式微時,埃及的宗教學者、知識分子即已呼籲哈里發體制的重建,這對阿拉伯穆斯林而言,有其特殊意義,因為古典時期的哈里發政權主控者一向是阿拉伯人。埃及伊斯蘭主義群體——穆斯林兄弟會(al-Ikhwan al-Muslimun, Muslim Brotherhood)在英國控管時期早已著手伊斯蘭復興改革運動,希望建立以伊斯蘭法為基礎的現代哈里發政權;但是其理念卻受到世俗統治者的批判排斥,進而受到打壓、屠殺,遂轉向以激進手段抗爭運作。經過長期的被迫害之後,兄弟會更加茁壯,開始檢討其運動途徑,亦試圖進入體制內進行改革,好不容易拿到政權後,卻被軍人發動政變推翻。埃及重回軍人獨裁的世俗化政治體制,伊斯蘭主義者在埃及被軍事政府大力掃蕩下,很多人被迫遠走他國。埃及伊斯蘭主義者的失敗,其造成原因相當複雜,最主要原因是執政後國家長久以來的經濟問題實無法純以宗教理想來解決,甚至伊斯蘭法的回復也急躁得不被人民接受。
突尼西亞的「阿拉伯之春」運動爆發後,表面上似乎已經轉向西方的民主制度,並被視為中東的民主模範生。透過民主選舉,伊斯蘭主義者進入了國會。突尼西亞在法國殖民勢力撤退後也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世俗化軍人獨裁統治,其間伊斯蘭主義者也積極提倡回歸伊斯蘭傳統,但成效不彰。在阿拉伯穆斯林國家中,受法國殖民影響較深的國家是突尼西亞,人民世俗化程度遠超過其他國家。也因為如此,普羅大眾較能接受西式的選舉制度。伊斯蘭主義者亦理解到這點,深覺若想全面執政必須修正其政治手段;甚至放棄「伊斯蘭主義」理念中較無法被一般大眾接納的意識形態。今日,突尼西亞的伊斯蘭主義也面臨了相當的困境;換言之,重新建立人民的伊斯蘭意識與價值觀不能以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經驗炮製之,而必須做相當的妥協,成為「不落實伊斯蘭理念的伊斯蘭主義者」。
伊斯蘭國的崛起見證、反映出極右激進伊斯蘭主義運動在諸多阿拉伯國家的被打壓與失敗。伊斯蘭國的領導者巴格達迪(al-Baghdadi)自稱為哈里發,他是伊拉克巴格達大學的伊斯蘭神學博士,具傳統宗教學者經學養成的背景。伊拉克獨立建國後歷經英國與美國的介入內政,本為歐斯曼帝國的屬地,獨立後成為世俗化的民族主義國家,伊斯蘭體制被破壞,伊斯蘭法無法落實。伊拉克境內的人民以什葉派穆斯林為主體,長期以來受到順尼穆斯林世俗化政府的打壓。在美國推翻沙達姆.胡笙(Sadam Husayn)(編按:坊間或譯為海珊)的政權後,扶持了什葉派穆斯林政權,進入新一波的政治與宗教的衝突。由於國家建設操在外國人手中,使得少數的順尼穆斯林激進分子結合了蓋達組織(al-Qa’idah)留下來的勢力,以武力對抗歐美支持的什葉派政權;這些激進分子更往西,挑戰敘利亞什葉派阿剌維政權(the Alawis)。從伊斯蘭國所顯示的文獻與網路聲明訊息觀之,巴格達迪企圖重建早期伍麥亞朝(the Umayyads, 661-750 AD)與阿巴斯朝(the Abbasids, 751-1258 AD)(編按:坊間或譯為阿拔斯朝)的哈里發體制,而他所秉持的理念正是中世紀神學家伊本.泰彌亞(Ibn Taymiyyah)的政治宗教理論;換言之,一切回歸到先知穆罕默德與正統哈里發時期的治國精神與體制,亦即伊斯蘭法必須嚴格的被執行。西方媒體對伊斯蘭國的報導極盡醜化,伊斯蘭國也藉西方媒體的報導突顯其自認的「伊斯蘭正統性」。而事實上,目前除了伊朗以外,幾乎所有的阿拉伯國家皆不能稱為Islamic State,因為最根本的伊斯蘭法並未全然落實。穆斯林國家統治者往往以國王(Malik)或部族首領(Amir, Shaykh)自居,宗教學者(‘Ulama’)並無發揮其應有功能以監督制衡統治者,甚至淪為統治者的工具。這也是巴格達迪以宗教學者身分挺身而出,推動他所信仰的哈里發體制之主要原因。
現今,當吾人在論述穆斯林國家的政治發展(即現代化運動)時,絕不能把宗教要素抽離。西方國家往往以其世俗政制的價值觀來看待當代穆斯林國家的發展,希望穆斯林國家能夠民主化,走西方的路線。穆斯林政治精英或知識分子不見得排斥民主制度,只不過伊斯蘭主義者強調「神意民主」(Theo-democracy),即民主制度必須建立在「神聖引導」(Divine Guidance)的基礎上。基於此,《古蘭經》、聖訓(al-Hadith)的教義必需被採納做為立法的基礎,這也是哈里發體制的真諦。哈彌德的書挑起了西方人處理伊斯蘭世界政治問題的神經。西方人喜歡談「政治伊斯蘭」,把政治置於伊斯蘭之上,甚至把政治從伊斯蘭全然生活之道的結構中抽離出來。《古蘭經》的教義規定了政治本為執行神旨意的手段,亦即伊斯蘭法必須以政治途徑來執行落實。因此我們可用「伊斯蘭政治」來說明當前伊斯蘭主義運動的本質,政治體制是其運動中的一個基礎面向。
Islamic Exceptionalism這本書檢視伊斯蘭在中東國家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重新解讀中東伊斯蘭主義運動,其所論述的例子呈現伊斯蘭運動的多元面貌。閱讀本書之後,吾人當可深入理解伊斯蘭主義運動並不能單純地與暴力畫上等號。事實上,作者也提出了中世紀、近代基督宗教運動所產生之惡劣鬥爭與暴力,非穆斯林在批判伊斯蘭主義為暴力前應檢討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在發展過程中,其鬥爭所產生的暴力與恐怖活動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總而言之,Islamic Exceptionalism論述了伊斯蘭主義運動正在改變中東國家的發展,其中文譯本的出版,當可增添台灣讀者對國際伊斯蘭運動的深入理解,並開拓世界觀。內文試閱
第一章 以屠殺為樂
有事情不大對勁,但是什麼呢?二○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我佇立在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中。在我身邊,數十萬埃及人把開羅商業區的街道擠得水泄不通。今夜,革命的第十八夜,群眾嘰嘰喳喳傳著總統穆巴拉克(Mubarak)即將下台、結束近三十年獨裁統治的消息。竊竊私語爆發成震耳欲聾的歡呼。這,無論這是什麼,正是他們翹首以待的。這場革命的年輕運動人士之一,名叫艾亞許(Abdelrahman Ayyash)的部落客,傳給我一則簡訊:「我們辦到了。」但興奮轉瞬即逝;往後四年,我們見到一場軍事政變、一連串大肆殺戮,接下來,獨裁政體回歸。而今天,艾亞許也如其他許多人一樣,在流亡中等待時機,渴望一個可能永不復返的埃及。
如果「阿拉伯之春」這個新詞真的有什麼意義,它意味著集體對政治失去信任。我還記得在二○一一年暴動開始之前,埃及人會以他們不同於一些鄰國、幾乎沒有政治暴力史的事實為傲。但二○一三年七月三日攆走該國首位民選總統的軍事政變,恐怕已永難挽回地改變了這點。這個人口最多、長期為中東地區領頭羊的阿拉伯國家,已任性地墮掉它的民主化胎兒,不管胎兒究竟有何缺陷。但話說回來,軍事政變是一回事;屠殺又是另一回事。
埃及首任民選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Mohamed Morsi)長期為穆斯林兄弟會要員,在他被推翻後的幾個星期內,數萬名支持者群集開羅的拉比亞阿達維亞(Rabia al-Adawiya,以下簡稱拉比亞)清真寺前大規模靜坐示威。埃及軍方宣布預備動用武力。全國坐立難安。沒有人知道軍方何時會展開行動。幾乎每天都有誤傳警報,有時甚至每小時就來一次。
等待屠殺是件怪事。當美國和歐洲的外交官拚最後一搏,急著說服埃及人打退堂鼓時,我在拉比亞花了點時間跟穆兄會的運動人士及領導人碰面。其中一位領導人是時任穆兄會政治部門、自由與正義黨(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副主席的伊薩姆.伊爾―伊里安(Essam El-Erian)。近十年來,我們已經會面多次,而當我們於那年八月初最後一次坐下來談時,他拒絕讓步。說阿拉伯語,但不時為了強調而穿插英文的他,堅稱穆兄會的成員已為最後的犧牲做好準備。另一名穆兄會高層,放棄在英國的成功事業,於革命後回到埃及的傑哈德.伊爾―哈達德(Gehad El-Haddad)則講述一位朋友最近被維安部隊槍殺的事。在這位年輕人臨終的那刻,他幾乎說不出話,但仍努力掙出伊斯蘭的信仰宣言:除了真主,沒有別的神明,而穆罕默德是神的使者。「別讓我的鮮血白流」,他告訴身邊的聚眾。他們也準備就義,而其中許多求仁得仁。幾天後,二○一三年八月十四日,當維安部隊化威脅為行動,超過八百位埃及人慘遭殺害。步兵、推土機和裝甲運兵車在黎明挾催淚瓦斯、彈丸槍和實彈長驅直入,強行清理營地。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稱此為「(埃及)現代史上最殘暴的濫殺」。
不到三年前,埃及才向世界證明何謂可能。突尼西亞,阿拉伯人起義的發祥地,是個人口僅一千萬、戰略及地理位置皆屬偏遠的國度。它受惠於高於多數阿拉伯國家的經濟成長及教育程度。假如起義從那裡開始,也在那裡終止,和平抗爭和政權更迭的可能性也許就容易遭到忽視。埃及改變了計算公式,推翻了「突尼西亞是地區例外」的說法。受到穆巴拉克下台的鼓舞,大規模抗議迅速蔓延到其他兩個國家——看似不可能成為政治動盪候選國的敘利亞和利比亞。二○一三年八月十四日,埃及再次首開先河,不過這一次埃及人——自相殘殺——給我們看的是黑暗得多,但同樣真實的畫面。
曾經,只有少數美國人聽過伊拉克與敘利亞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或ISIS——不久即重新命名,直呼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情況在二○一四年夏天驟然一變,先是伊拉克第二大城摩蘇爾(Mosul)淪陷,第一波一千名左右的戰士擊潰一支兵力三萬的伊拉克部隊。再來是令人震驚的美國記者斬首事件,以及二○一五年十一月巴黎一百三十位平民遇害(這是自二次大戰以來法國遭受最嚴重的攻擊)——將伊斯蘭國的名聲定調為慘無人道。似乎一夕之間,這個遜尼派極端團體成了人人聞之色變的新敵人。
我們很容易譴責伊斯蘭國邪惡,因為它確實為惡不悛。該團體的所作所為,大多充斥著草菅人命、熱中濫殺的心態。但後阿拉伯之春時代之所以會如此動盪不安,是因為一種更平庸的惡似乎在四處蔓延,這是種讓本性善良的人們反目成仇的惡,讓人不僅接受流血是衝突不可避免的代價,更對此深信不疑,甚至以此為樂。
這是一個讓區域陷入瘋狂的故事。我們很容易覺得這一切莫名其妙,然後撇過頭去,無視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自相殘殺。但故事仍有一部分是可以解釋的。或者,我們必須試著去解釋。想了解看似超乎理解的事物,這種衝動至關重要,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刻。專欄作家菲利普.古勒維奇(Philip Gourevitch)貼切地稱此為:「想像真相究竟為何的特殊必要性。」
基於為時超過十年的調查研究,包括親身在中東地區居住、走訪、研究六年多,這本書不僅試圖釐清那些令人悲傷、戰慄的事件,更想要理解思想的力量,以及思想在那些撼動中東秩序基礎的生存戰鬥(existential battle)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本書中,我將回到一些反覆出現、讓我竭盡心力的主題和問題。例如,在試著了解中東戰火、伊斯蘭國崛起,以及對於看似微不足道之事物(如穆罕默德先知的漫畫)的文化分歧時,伊斯蘭究竟有多重要?那到底是關乎「宗教」還是「政治」的事?而當這兩者在信仰者的心靈與腦海緊緊交纏,我們有辦法把它們分開嗎?
要了解今天看似無解的衝突,我們起碼得回溯至一九二四年,也就是最後一個哈里發政權(caliphate)被正式廢除的那一年。過去,哈里發體制是根據伊斯蘭律法和傳統統治的政治實體,而「建立哈里發」則是「穆斯林教眾的心靈一統,需要政治上的表現」的概念。自哈里發體制廢止後,建立正統政治秩序的爭鬥就如火如荼,激烈程度不一。爭鬥的焦點正是宗教與宗教該在政治上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阿拉伯之春和其後續的騷亂就是最新一次的例證,證明何謂公民、何謂國家等最基本的問題,且始終無法解決。
對現代人而言,一九二四年或許看來已經像古代史,但我必須再往前追——追到西元七世紀伊斯蘭教創立時。有兩個彼此相關的論點構成本書第一部分的核心。一是伊斯蘭教與政治的關係非常特殊。伊斯蘭是特別的。這個差異對中東的未來,乃至我們每個人身處的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無可否認,這是一個有爭議、甚至令人不安的說法,特別是在歐美反穆斯林情緒高漲的脈絡中。但「伊斯蘭特殊論」(Islamic exceptionalism)其實無關好壞。事情就是那樣,而我們需要理解它、尊重它,就算它與我們的希望和偏好背道而馳。
其次,因為伊斯蘭教和政治的關係非常特殊,重演西方模式——宗教改革繼啟蒙運動後發生,將宗教逐步推往私人領域——是不可能的。伊斯蘭是截然不同的宗教,創建和演化過程皆與基督教截然不同,要它依循基督教路線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種怪異的傲慢。我們並不一致,而更重要的是,我們為什麼該一致?
如果穆斯林,特別是伊斯蘭主義者,看待經文比基督徒來得「嚴肅」,這點會如何彰顯於日常政治呢?當觀察者討論中東衝突的根源時,常提到統治權或正當性的危機,或者兩者皆是。但如果我們循著因果關係往下走,問題仍未解答:中東究竟為什麼會深受缺乏正統秩序所苦呢?我認為正當性的挫敗,與始終無法釐清伊斯蘭和國家的關係息息相關。
並非沒有人嘗試。本書第二部分就將探討,要解決伊斯蘭國家所面臨的兩難,可能有哪些截然不同的模式。我選用「特殊」一詞,部分是為了避免妄加評判。我認為既為特例,那本身就無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那取決於伊斯蘭和國家問題的實際情況。在尋找解方時,廣納各種途徑與策略的主流伊斯蘭主義運動,乍看是希望所繫,但那些途徑與策略各自有不足之處。
在這裡,主流伊斯蘭主義者的定義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分會或衍生組織。穆斯林兄弟會在一九二八年由名為哈珊.班納(Hassan al-Banna)的學校教師於埃及創立,堪稱所有伊斯蘭主義運動之母。伊斯蘭主義者希望融合前現代和現代,融合東方與西方。從這個意義來看,這與一般人想像相反,伊斯蘭主義者不見得想回到七世紀的阿拉伯。如我們即將看到的,他們非常現代,或許太現代了。他們獨樹一格的特色包括漸進主義(gradualism,從歷史觀點來看相當於避免革命)、欣然接受議會政治,以及願意在現有的國家結構內工作,甚至不排斥世俗的國家結構。伊斯蘭主義運動相信伊斯蘭宗教或伊斯蘭律法應在政治生活中扮演核心角色,而且要為這些公共領域的目標明確地建立起組織。雖然他們當前的表現不若激進派搶眼,但最具政治影響力的伊斯蘭主義團體向來是主流、非暴力的派別,因此,就算他們不是今天上最多頭條的伊斯蘭主義運動,仍值得我們投入相當程度的關注。
我會先探討基本的穆兄會模式,全球數十個國家都有各自受穆兄會啟發而成立的組織。接著我會將焦點轉向世俗化脈絡下的伊斯蘭主義者所採取較地方性的策略,即著眼於已和強迫世俗化交手數十年的土耳其和突尼西亞。這兩個國家被譽為伊斯蘭和民主制度和解的模範。有趣的是,雖有世俗化的脈絡,這兩國也是少數由伊斯蘭主義政黨執政的中東國家。不過,基於種種原因,這些「溫和」、較「親世俗」的伊斯蘭主義者,尚未能進一步推展成功的伊斯蘭綜合體(Islamic synthesis),有時甚至使得原本希望解決的緊張局面雪上加霜。我會詳盡探討這些引人入勝的案例,並聚焦在幾位最有趣、最重要、形塑伊斯蘭內部政教辯論的人物上。
阿拉伯之春未能造就正統、穩定的政治秩序,反倒為更激進、在暴力與專制中鍛造路線的組織開闢空間。伊斯蘭國,即ISIS的「反模式」(countermodel)是第七章的焦點。這個極端團體在二○一四年夏季的迅速崛起或許讓觀察家猝不及防,但如果歷史的弧線理當趨向正義,像伊斯蘭國這樣的組織在這個世紀興起,卻是令人意外的適切。自一九二四年哈里發體制被廢,從來沒有嚴肅、持續的重建哈里發體制行動。如今,伊斯蘭國——有分布甚廣的作戰分支,或「省」——可謂拔得頭籌。不僅如此,伊斯蘭國還是近數十年來可辨識之伊斯蘭主義統治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就算這裡的標準相對低)。伊斯蘭國相對認真地看待治理和制度建立,成效也優於世人預期。相較於恐怖主義,這或許才是這個團體最重要的特徵,也使它成為更值得尊敬——也更危險——的敵人。它的統治模式或許在許多方面令人驚駭,但確實是種與眾不同的模式。而與穆兄會和其他主流伊斯蘭主義運動呈現鮮明對比的是,伊斯蘭國對中東現有的國家結構幾乎不感興趣。
對伊斯蘭國的強硬派而言,最後一個哈里發政權是鄂圖曼哈里發王朝,但最後一個模範哈里發體制則是先知穆罕默德四個蒙正確指引(righteously guided)門徒的哈里發政權——四人都曾以哈里發的身分短暫治理過一個領土不斷擴張的帝國(其中三人遇刺身亡)。不過,伊斯蘭國並未因此就不把鄂圖曼哈里發王朝的解體,和被人為分割成數個專制國家的結局,視為現代的原罪。現代國家愈是仰賴世俗的公民觀念、愈是倚靠制定法律的議會而非真主,就愈不見容於伊斯蘭國完整的真主統治觀。真主,唯獨真主,是唯一的立法者。在穆兄會和它在土耳其、突尼西亞和約旦各國的同志,力圖調和前現代的伊斯蘭律法和現代多元、民主觀念之際,伊斯蘭國卻大搖大擺地浸淫於反對多元民主的作為,而其成果可能既恐怖又有效。而有時,有效正是因為恐怖。
在一片暴虐和混亂中,不管穆斯林或非穆斯林都試著了解伊斯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應該扮演的角色。在討論伊斯蘭民主化過程中的正反模式時,我希望提供個架構來思考伊斯蘭教、伊斯蘭主義和它們與政治的關係,以及或許最受爭議的——與現代民族國家的關係。
如果伊斯蘭可能於可見的未來在中東政治擔綱份量超重的角色——我認為它會——這一點就有非常重大的意涵。那意味著與其期待可能永遠不會來臨的宗教改革,我們應該認清伊斯蘭很特別的事實,且盡最大的能力和意願接受它、習慣它。這不是件容易的事。誠如馬克.里拉(Mark Lilla)所言:「雖然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基本教義派,但我們無法理解神學理念還會激起彌賽亞的熱情、使社會崩壞。我們以為這再也不可能發生。」但這絕對可能。伊斯蘭從創教以來所沿用與政治有關,且賦與政治意義的語言——數億人迄今仍堅信不移的語言——乍聽下也許光怪陸離,但那只代表外人必須付出額外的心力加以理解。而那一點,在某些方面,正是我的工作最具挑戰性,但收穫也最豐碩的部分:接觸徹底不同的事物。延伸內容
◆編輯推薦——本篇收錄於第583期城邦讀饗報,立即閱讀更多內容!GO
◎文/馬可孛羅編輯 邱建智
近一、兩年來世界局勢仍相當不平靜,以美國川普為首的右翼民族主義政黨在世界各地都掀起波瀾,這多少跟近年來崛起的伊斯蘭國、歐洲難民危機有關,它某種程度加劇了歐洲各國的社會、經濟問題、民粹主義崛起,也加深基督教世界(或稱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誤解與衝突。
《你所不知道的伊斯蘭》是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研究員夏迪.哈彌德的最新著作,這本書主要想探討兩個問題,一是導正人們單一的西方視角,認為伊斯蘭世界理應走向民主改革之路,作者認為這忽視了伊斯蘭文化的內在發展理論,不理解伊斯蘭宗教與政治、社會的不可切割性。第二,作者細究伊斯蘭主義運動的多樣性,列舉包括在埃及、土耳其、突尼西亞、伊斯蘭國的發展模式,其中有傳統穆斯林在面對西方強勢文化下的焦慮與困惑,也有新時代的伊斯蘭主義者在改革創新之餘也要維繫古老傳統的努力。本書可幫助理解國際伊斯蘭運動的發展狀況,也可幫助讀者打開另一扇認識伊斯蘭世界的門窗。
立即訂閱城邦讀饗報!GO作者資料
夏迪.哈彌德(Shadi Hamid)
埃及裔美國籍中東政治研究學者,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國─伊斯蘭世界關係計畫的資深研究員,亦為《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特約作家,另著有《權力的誘惑:新中東世界的伊斯蘭主義者和不自由的民主》(Temptations of Power: Islamists and Illiberal Democracy in a New Middle East),現居於華盛頓特區。
注意事項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