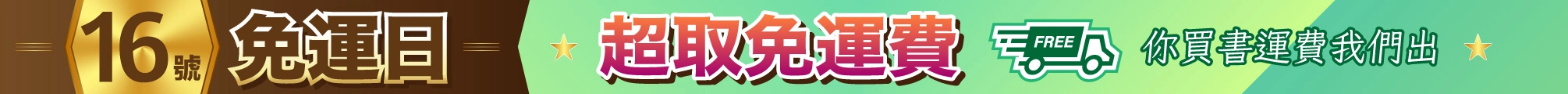-
千千萬萬都是你
-
滿分贗品(限)【限量贈品版】
-
重疊愛戀(限)【限量贈品版】
-
風知道的事
-
中場過冬(限量贈品版)【網路超人氣作家妄言熱戀.限制級極致虐心酥慾力作】
-
鬼樂透(文策院影視計畫改編原著全新增修完整版)
-
水魅雷普利【雷普利系列05】(限量附贈海史密斯逝世30週年紀念版「作者親繪貓咪 」書籤):犯罪小說史上最令人不安的經典
-
旅行之木:日本國寶級生態攝影家星野道夫33篇追尋極北大地之夢的旅行手札
-
跟蹤雷普利【雷普利系列04】(限量附贈海史密斯逝世30週年紀念版「作者親繪貓咪 」書籤):犯罪小說史上最令人不安的經典
-
大腦切除師(榮獲諾貝爾獎的「奇蹟器官手術」黑歷史!美國亞馬遜破萬讀者好評,改編自真實事件,揭露醫學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內容簡介
導讀
※本文內容涉及《雨的祈禱》一書情節,請自行斟酌是否繼續閱讀。
你在期待什麼?一個怪物嗎? ──《8 mm》
上個世紀末,1999年,有部叫做《八厘米》(8 mm)的電影上檔。
新寡不久的社會名流夫人在整理先夫遺物時,發現保險櫃裡有盤八厘米錄影帶,裡頭錄製了一個年輕女孩被殘忍虐殺的經過,女孩痛苦的反應看起來真實駭人,一點兒都不像是在演戲。嚇壞了的寡婦找來一名叫做湯姆.威勒(尼可拉斯凱吉飾演)的私家偵探,要他去查明錄影帶的真相;威勒從虐殺影片當中的蛛絲馬跡一路追索,找到了女孩的母親、接觸了特殊癖好的色情電影產業,生活的內容開始從小鎮偵探的簡單色彩,漸漸染上他從未想像過的黑暗。
《八厘米》這部電影整體而論不算傑出,但其中有兩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威勒這個角色對案件的執迷。威勒原來只是個尋常偵探,有支持自己的妻子(凱瑟琳基納飾演),還有個剛出生的女兒,承辦的事件不會太複雜龐大,日子過得也平凡簡單;接了這宗案子之後,他的態度從交差了事到執拗沉迷,逐漸背離家人妻女,甚至在旁人都認為他任務完成、可以停手的當口,他仍固執地追查,想要找出影片中那個戴著頭套、真正下手殺人的凶手身分。
探員深入闇暗事件後變得異常偏執,這樣的設定在很多故事裡可以讀到。
例如詹姆士.艾洛伊(James Ellroy)的《黑色大理花》(The Black Dahlia)(電影版時代感覺設計得挺好,但情節改編和敘事節奏卻會令人皺眉)或者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的《屠宰場之舞》(A Dance at the Slaughterhouse)(這個故事的起點也與虐殺影片有關,不過不但發現的方式曲折許多、故事情節複雜許多,而且早在1991年就已經出版了);探員或偵探們之所以不惜忽略自己原來的生活、甚或違背某些處事原則地探究,可能是賭氣似的拚命,可能是個性使然,以《八厘米》這個故事而言,也可能是因為威勒想要親眼看看:製造出如此病態歪邪情境的,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
《八厘米》裡值得注意的第二件事,就在此處。
電影即將結束時,威勒遇上了他一心查緝的凶嫌,扭打之後扯下對方的頭套,接著一愣──發愣的原因並非凶嫌是哪個令他意外的人物,也不是因為凶嫌的長相有什麼特殊之處,威勒發愣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凶嫌看起來實在太平常了。在《八厘米》最初的劇本中,編劇並沒有打算讓觀眾看見凶嫌的模樣,或許是想要藉此留下某種想像空間;但最後在戲院上映的版本裡,觀眾不但瞧見凶嫌的樣子,還聽到頭套剛被扯掉的凶嫌用一種不以為然的口氣,對一臉驚愕的威勒說:「你在期待什麼?一個怪物嗎?」
讀完《雨的祈禱》(Prayers for Rain),忽然想起《八厘米》中的這個畫面。
《雨的祈禱》是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以派崔克‧肯錫(Patrick Kenzie)及安琪拉‧珍納洛(Angela Gennero,暱稱「安琪」)為男女主角的第五本系列作品。故事開始時,派崔克與一名天真單純的女孩見面,受僱去警告一個持續騷擾她的混蛋,派崔克簡單直接地完成任務,以為女孩可以就此高枕無憂;六個月後,派崔克從收音機上聽到一則新聞,指稱一名全裸女子自波士頓地標建築海關大樓的觀景臺上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的性命,他訝異地發現,這名跳樓自殺的裸女,居然就是六個月前來找自己幫忙的純真女孩,稍一探查,他還發覺:女孩在跳樓前已經染上藥癮,前一陣子甚至曾因賣淫被捕。究竟發生了什麼,才讓女孩的人生在半年之內急轉直下,最後選擇自我了斷?派崔克開始著手調查,並找來已經拆夥的搭檔安琪幫忙,不料麻煩也隨之而至。
驗屍結果確認女孩是自殺的,但派崔克為何仍執意追查?
有一種可能是罪惡感作祟──在派崔克解決騷擾事件的數週之後,女孩曾經打電話給他,派崔克當時因故沒接,後來也忘了回電──派崔克在女孩亡故之後想起這事,不免覺得有點愧疚。但說實在話,人都死了,就算派崔克查出那六個月發生什麼事,也已經無法挽回什麼;況且,在追查過程當中,派崔克不停面對種種威脅及危險(有的針對他的夥伴,有的則針對他自己),卻仍沒有就此抽手。派崔克的所做所為,遠比為了想彌補自己沒與對方聯絡所生的遺憾,還要多上許多倍,而這樣的行為模式,與《八厘米》中威勒及其他前述小說探員的執迷,有個共同的核心元素。
這個核心元素,可以簡單地稱之為「正義」
且慢;千萬不要因為這個詞就聯想到諸如「邪不勝正」、「罪犯伏法」之類說法當中的那種「正義」──被包覆在這些角色行動核心的「正義」其實不一定完全合法、不一定合乎社會大眾的道德判準、不一定與所有惡念都相對而立,也不一定會讓所有人心服口服地認為「這是對的!」;這些角色們的正義帶著濃厚的私人色彩,服膺的不是制定的法條或者從眾的規範,而是他們自己內裡的一套處世標準。依著這套正義準則行事,讓他們同時成為某種型式的法外之徒以及某種型式的英雄,在各種法律規條已經放手的那個空間裡,發出某些吶喊──諷刺的是,這樣不怎麼合乎規矩的吶喊,反而真正彰顯了人性當中,最可貴的那個部分。
從《派崔克/安琪》系列的前幾本作品當中,其實都可以讀出這樣的嘶吼。
每每愈挖愈深、翻出一堆骯髒暗裡的系列作品第一部是《戰前酒》(A Drink Before The War):派崔克與安琪這對搭檔首度登場,受三位波士頓當地重量級政壇人物的託囑,尋找一個曠職的黑人清潔婦,原因自然不是清潔婦上班缺勤,而是清潔婦在曠職之前,偷走了一個參議員的機密文件;擅長尋人的偵探二人組找到清潔婦的藏身處,對方指稱自己拿走的不是什麼機密文件,而是別的資料,就在派崔克與清潔婦一同去取資料時,遇上伏擊。第二部作品《黑暗,帶我走》(Darkness, Take My Hand)從一位被黑幫分子威脅的心理醫師來電開始:這位心理醫生接到黑幫份子的電話威脅,因為擔心自己兒子的安危,輾轉找上派崔克介入調查;經過一番查訪、以為可以交差了事的時候,派崔克才發覺不但安琪的丈夫被捲進事件當中,連自己的女友與女友的孩子,可能都因此面臨生命危險。 在第三部作品《聖潔之罪》(Sacred)的開場,這對搭檔被綁架了。
綁架他們的是一個古怪的富豪,打算委任他們去找自己失蹤的女兒,但因為派崔克與安琪那陣子都不想接案,只好使出激進手段。他們發現其實富豪先前找過更有規模的徵信社調查此事,負責本案的偵探也在查案時卻也失去蹤影,而這位失蹤的探員,不但是安琪的舊識,更是引領派崔克入行、亦師亦兄的前輩。派崔克和安琪接下任務,追查到一個紓壓靜修公司,本以為會牽扯企業內莫,不料劇情至此一轉,朝一個令人料想不到的方向走去。在第四部作品《再見寶貝,再見》(Gone, Baby, Gone)中,派崔克與安琪接受一名失蹤兒童的舅舅及舅媽請託協助調查,加入一宗全波士頓都在關注的兒童失蹤案件搜尋行列,原以為破案無望,卻在幾經轉折之後,發覺他們必須面對的,是更龐大的道德與人性選擇。
除了不屈不撓的追索態度之外,勒翰在系列作品當中,還有幾個一再出現的重要議題。
最明顯的,是勒翰對兒童相關問題的關注。包括《雨的祈禱》在內的五部系列作品以及《神祕河流》(Mystic River)、《隔離島》(Shutter Island)兩部獨立作品,雖然佔比不同,但都提及了兒童議題:兒童的性侵害或性交易、兒童的誘拐及謀殺、兒童在成長環境中遭遇的暴力,以及兒童被忽視或不當教養產生的偏差。在成為專職作家之前,勒翰曾經擔任過諮詢受虐兒童的心理輔導人員,在開始撰寫小說之後,現實當中兒童所面臨的種種危機,仍是他長期關心的焦點。
另一個重要議題,則是感情與暴力之間的牽扯。
雖然看起來似乎是兩回事,但事實上,所有感情當中都不免帶著暴烈的層面,有的會外顯成拳腳相向,有的會內化成言語施壓。畢竟,再怎麼自以為無私的感情,總還有著為自己著想的面向,而面對這樣的情況,感情就會無可避免地出現自私、殘酷、盲目及不可親的現實臉孔。再者,派崔克與安琪的搭檔關係也不斷出現耐人尋味的變化;他們兩個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好友,但在《戰前酒》的故事開始時,這兩人並不是情侶關係:彼時安琪已經嫁人,而就安琪的說法,派崔克似乎頗頻繁地更換女友。每次共同經歷事件,兩人的關係就會產生不同的轉變,這除增加閱讀系列作品的趣味之外,也可以對照出每回事件對兩人內心的衝擊,以及這些反映人性的案件內裡,讓他們怎麼重新審視感情當中的種種層面。
貫串整個系列的,還有家暴議題。
除了兒童可能遇上的各種型式家暴狀況之外,在《戰前酒》當中,安琪也有個會對她施暴的丈夫。在故事主述者派崔克眼中,安琪是個漂亮、聰慧、幽默、迷人,槍法比自己更準確的新時代女性,但這樣的女性角色,面對家暴的丈夫,仍會顯出因為情感牽扯而生出的迷惘與糊塗。這不但道出了現實當中某部分的家暴真相,也讓前述的幾個議題相互絞揉,成為一個堅實完整、能夠利用故事情節從各個面向觀察討論的主題。
針對這樣的主題,在《雨的祈禱》結局時分,勒翰提出了另一個角度的論點。
當派崔克找上真凶,後者以雙親的逼迫來替自己的所做所為開脫,自認為慘狀無人能比地向派崔克述說,沒想到派崔克本身其實就是個童年受虐的孩子(這點在《戰前酒》裡就已提及):派崔克的父親曾用熨斗在他身上烙下疤痕、打得他入院兩次,而且幾乎每週都有一次會揍得他連廁所都不能上。但無論是被父親痛揍的派崔克或者是承受丈夫拳腳的安琪,都沒有因此認同人心的黑暗,相反的,他們選擇建立自己的價值觀、與這些靈魂當中的污穢奮力對抗。
是的;在訴說種種可能造成重大歪曲的殘酷之後,勒翰並沒有忘記:一個人要怎麼活著,其實仍要自己決定。
《雨的祈禱》最後幾段,真凶以一個虛構的寓言故事向派崔克做出不算自白的自白,從那個明顯可以對號入座的寓言中,可以發現悲劇的主因,其實是真凶自以為是的偏執妄念:當他自認被父親嫌棄,又因妹妹的意外而被全家怪罪之後,偏差的執念便一路將他拖進墨黑的深淵。假使他的念頭稍轉、假使他的心緒稍寬,一切就會有所不同。當然,這些被他認定有愧於己的家人,或許都不能說完全沒有責任,但讓自己看起來人畜無害、實則悄悄在內心餵養怪物的生活方式,其實還是真凶自己的選擇。《八厘米》的凶手對 Welles 自承沒有什麼童年陰影,既沒被性侵也沒被虐待,會在虐殺影片中動手行凶,完全出於自己歪斜的癖好;如此看來,《雨的祈禱》中把罪過歸咎於家人的真凶,其實更為卑劣,也更為膽怯。
頭套下沒有怪物,因為怪物其實住在深深的人心內裡;而勒翰的故事,則將覆著它們的表皮直接掀開。
從達許.漢密特(Dashiell Hammett)、雷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羅斯.麥唐諾(Ross MacDonald)、勞倫斯.卜洛克、詹姆士.艾波伊到丹尼斯.勒翰,這些作家筆下被劃歸為「冷硬(Hard-Boiled)」派的故事,幾乎都有這樣的特質:揭開不同階層不同人物的種種表象,移來光源,將不堪的人性亮晃晃地照映出來,讓讀者們清楚地認知:所謂怪物,其實正是人類自己某些特質的聚合。
或許有人要問:世界很糟,人性很爛,這些在現實世界天天上演,何需再花筆墨闡述?
因為這些作者利用故事將世界裡子的髒污翻轉出來的時候,總還會在裡頭安置幾個疲憊、頹唐、不全然符合社會標準、嘴上不說但心裡一直有所堅持的角色,不自覺地撐起全世界的不仁不義,鍥而不捨地前進想要證明一些什麼;他們對人性大多沒什麼信心,但他們的所做所為,卻是人性當中,某種良善的現世證明。這些故事雖然昭顯了殘酷的現實,卻會在情節行進的時候,開始與之抗爭;閱讀這些故事,重點並不在聽作者訴說人性當中的種種黯影,而在期待闇黑之境裡,他們燃起的小小光亮──彷彿在大旱之際,某種即將飄雨的微渺徵兆,那是一種慰藉,也是一種希望。
只要落下第一滴雨點,世界,就有可能變得不再一樣。
內文試閱
我第一次見到凱倫‧尼寇斯時,覺得她是那種會燙襪子的女人。
她是個嬌小的金髮女郎,從一輛鮮綠色的一九九八年款福斯金龜車下來,此時巴巴和我穿過馬路,手裡拿著我們早晨的咖啡,朝聖巴托洛穆教堂走去。那是二月,不過那年的冬天忘了亮相。除了一場暴風雪和幾天低過攝氏零下十度以外,這個冬天簡直近乎暖和。今天氣溫有個八、九度,而現在還只是上午十點。隨你怎麼說全球暖化有多糟,只要讓我不必鏟門口的雪,我就歡迎。
儘管上午的太陽沒那麼大,凱倫‧尼寇斯還是一手遮在眉毛上方,猶豫地朝我微笑。
「肯錫先生嗎?」
我秀給她一個吃素乖兒子的純良微笑,伸出一隻手。「尼寇斯小姐嗎?」
她不知怎地笑起來。「沒錯,叫我凱倫吧。我早到了。」
她的手握住我的,感覺好滑好嫩,簡直像戴著手套似的。「叫我派崔克吧。這位是羅格斯基先生。」
巴巴喉嚨裡咕噥一聲,喝了一大口咖啡。
凱倫‧尼寇斯的手抽回,輕輕往後縮了一下,好像害怕必須跟巴巴握手。怕如果握手的話,手可能就抽不回來了。
她穿了一件褐色的麂皮夾克,長度到大腿的一半,罩著裡頭的水手領粗線針織炭灰色毛衣,俐落的藍色牛仔褲,亮白的銳跑運動鞋。從她全身上下來看,彷彿方圓十哩內都沒有一絲皺紋、沒有一點汙漬,或一縷塵埃。
她纖細的手指放在光滑的頸項上。「兩個真正的私家偵探,哇。」她溫柔的藍色眼睛隨著小巧的鼻子皺起來,又笑了。
「我是私家偵探,」我說,「他只是幫忙打雜的。」
巴巴喉嚨裡又咕噥了一聲,作勢要踹我。
「別激動,小子,」我說,「乖一點。」
巴巴又喝了口咖啡。
凱倫‧尼寇斯的表情好像覺得自己赴約是個錯誤,於是我決定不帶她去我位於鐘樓上頭的辦公室了。如果有人對於雇用我有疑慮,帶他們去鐘樓通常不是高明的公關手腕。
今天星期六,學校不上課,空氣潮溼,沒有一絲寒意,於是凱倫‧尼寇斯、巴巴和我就走向鐘樓對面校園裡的一張長椅。我坐下,凱倫‧尼寇斯用一條乾淨無瑕的白手帕撢了撢長椅表面的灰塵,然後也坐下。巴巴看著空間有限的長椅皺眉頭,又朝我皺眉頭,然後坐在我們面前的地上,兩腿盤起,期待地朝上看著我。
「乖狗狗。」我說。
巴巴狠狠看了我一眼,意思是等這個社交會面結束以後,他就要找我算帳。
「尼寇斯小姐,」我說,「你從哪裡打聽到我的?」
她的目光從巴巴身上移開,轉而看著我的眼睛,一時之間完全不知所措。她的金髮剪得很短,像個小男孩,讓我想到以前看過那些一九二○年代柏林女人的照片。儘管塑形髮膠讓她的一頭短髮緊貼著頭皮,除非靠近運作中的噴射引擎才可能弄亂,但她左耳後頭還是夾了髮夾,就在頭髮分邊處的下方,一根黑色的女用髮夾,上頭有個金龜蟲圖樣。
她睜著大而清澈的藍色眼珠,又緊張地短促一笑。「我男朋友。」
「那他的名字是⋯⋯」我說,猜想叫什麼塔德或泰伊或杭特之類的。
「大衛‧威特若。」
我的通靈能力還真遜。
「恐怕我沒聽說過他。」
「他認識一個以前跟你工作過的。好像是個女人?」
巴巴抬起頭瞪著我。巴巴把一切都怪罪到我頭上,因為安琪終止我們的合夥關係,搬離這一帶,買了一輛本田汽車,穿起名牌的安‧克萊恩(Anne Klein)套裝,基本上就是不再跟我們混一道了。
「安琪‧珍納洛?」我問凱倫‧尼寇斯。
她笑了。「對。她就叫這個名字。」
巴巴又從喉嚨裡咕噥了一聲。我看很快地,他就會開始對著月亮嚎叫了。
「那為什麼你需要找個私家偵探,尼寇斯小姐?」
「叫我凱倫。」她在長椅上轉過身子來面對著我,把一綹不存在的頭髮塞到耳後。
「凱倫,為什麼你需要找個私家偵探?」
她緊閉的嘴唇微彎,掠過一抹哀傷的微笑。她低頭看著膝蓋一會兒。「我平常去的健身房,那裡有個傢伙?」
我點點頭。
她吞嚥了一口。我想她是希望我能從她那個句子,就猜出所有的故事。我很確定她接下來就會告訴我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更確定那頂多不過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他在追我,跟蹤我到停車場。一開始只不過是,你知道,有點煩?」她抬起頭搜尋我的眼睛,希望我聽懂了。「接下來就更離譜了。他開始打電話到我家。我在健身房開始躲著他,但有兩次我看到他把車停在我家外頭。最後大衛受夠了,出去找他談。他一概否認,然後還威脅大衛。」她眨眨眼,左手手指扭絞著,攢在右手的拳頭裡。「大衛不是那種體型很⋯⋯有威嚇性的?這個字眼對嗎?」
我點點頭。
「所以,科迪—那是他的名字,科迪‧佛克—他嘲笑大衛,當天晚上照樣打電話到我家來。」
科迪。就一般基本的原則來說,我已經開始討厭他了。
「他打電話來,說他知道我有多想要,說我這輩子大概從來沒有好好,呃,好—」 「打炮。」巴巴說。
她瑟縮了一下,瞥了他一眼,然後目光迅速回到我身上。「沒錯,說我這輩子從沒有好好⋯⋯那個過。又說他知道我暗自希望他給我一次。於是我在他車上放了一張字條。我知道這樣很蠢,但我⋯⋯反正我放了字條就是了。」
她手伸進皮包裡,掏出一張縐巴巴的紫色便條紙。以完美無瑕的草寫體寫著:
佛克先生,
請不要打攪我。
凱倫‧尼寇斯
「下一回我去健身房,」她說,「離開時去開車,發現他把這張字條夾在我的擋風玻璃上,就跟我留給他字條是同樣的位置。肯錫先生,你把字條翻面,就可以看到他寫的。」她指著我手裡的那張紙。
不。
我真的開始討厭這個混帳了。
「然後到了昨天。」她雙眼含淚,吞嚥了好幾次,柔軟的白色喉頭顫抖得好厲害。
我一手放在她手上,她手指緊緊蜷縮著。
「他做了什麼?」我說。
她嘴巴吸了口氣,我聽得到她喉頭一聲哽咽。「他惡意破壞我的車。」
巴巴和我都朝停在校園入口的那輛鮮綠色福斯金龜車看了一眼。那車看起來像是才剛出廠的,車裡頭大概還有那種新車的氣味。
「那輛車?」我說。
「什麼?」她隨著我的目光看過去。「啊,不,不是。那是大衛的車。」
「大男人?」巴巴說。「大男人開那種車?」
我朝他搖搖頭。
巴巴沉下臉,低頭看著腳上的戰鬥靴,然後盤坐起來。
凱倫搖搖頭,好像要澄清。「我開的是一輛豐田Corolla。我原先想要Camry,但是我們買不起。大衛的新事業才剛開始,我們都還有學生貸款沒繳清,於是我買了Corolla。結果現在車子毀了。他在整輛車上頭倒了強酸,戳破了水箱。技工說他在引擎裡面倒了糖漿。」
「你報警了嗎?」
她點點頭,小小的身子顫抖著。「沒有證據能證明是他做的。他告訴警察,他那天晚上去看電影了,有證人看到他進去電影院又出來。他⋯⋯」她的臉整個漲紅又垮掉。「他們動不了他,保險公司也不肯理賠。」
巴巴抬起頭,朝我看著。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收到我上次繳的保險費。但我⋯⋯我寄了。我三個星期前就寄出去了。他們說他們寄了繳費通知,但我從來沒收到過。然後,然後⋯⋯」她低下頭,淚水落在膝上。
她一定有不少絨毛玩具,我很確定。她被破壞的Corolla保險桿上一定貼了笑臉貼紙,或代表基督徒的耶穌魚標誌。她愛看約翰‧葛里遜的小說,喜歡聽抒情搖滾樂,喜歡參加朋友婚前的告別單身派對,而且從來沒看過史派克‧李的電影。
她從沒想過,這類事情會發生在她身上。
「凱倫,」我輕聲說,「你的保險公司是哪家?」
她抬起頭,用手背擦掉淚水。「國家保險公司。」
「那你寄保險費支票,是哪個郵局處理的?」
「唔,我住在牛頓市的上瀑村,」她說,「不過我不確定是在那邊寄的。我男朋友呢?」她低頭看了看自己潔白無瑕的運動鞋,好像很羞愧。「他住在後灣區,我常常待在那邊。」
她講得好像那是一種罪,我不禁好奇,是什麼地方會生養出她這樣的人,不曉得有沒有種子,可以讓我生養出這種女兒,而我又該怎麼去弄到這類種子。
「你之前遲繳過保險費嗎?」
她搖搖頭。「從來沒有。」
「你在那家公司保險有多久了?」
「從我大學畢業以後,七年了。」
「科迪‧佛克住在哪裡?」
她兩手的手腕背部輕按眼睛,好確定把淚水擦乾了。她沒化妝,所以也不會掉妝。她那種溫和的美,就像樂爽美(Noxzema)滋潤洗面乳的廣告女郎一樣。
「不曉得。不過他每天晚上七點都在健身房。」
「哪個健身房?」
「水城的奧本山俱樂部。」她咬著下唇,想擠出類似香皂廣告女郎的微笑。「我覺得好荒謬。」
「尼寇斯小姐,」我說,「你不懂得怎麼對付科迪‧佛克這種人,這本來就是應該的。你明白嗎?沒有人應該懂得。他只不過是個壞人,這不是你做錯什麼而造成的。是他的錯。」
「是嗎?」她總算設法露出微笑,但眼裡仍泛著困惑的淚光。
「沒錯。他是壞人。他喜歡逼得別人害怕。」
「是啊。」她點點頭。「從他眼裡就看得出來。只要他哪天晚上在停車場搞得我愈不安,他好像就會愈開心。」
巴巴低笑著說。「要比不安?等著我去見見這個科迪就知道了。」
凱倫‧尼寇斯看著巴巴,一時之間似乎憐憫起科迪了。
回到辦公室,我撥個電話找我的律師查斯維克‧哈特曼。
凱倫‧尼寇斯開著他男朋友的福斯車離開了。我叫她直接開到她的保險公司,補開一張保險費支票。她說他們不會理賠,我保證等她人到那裡的時候,他們就會了。她說她不曉得是不是付得出我的費用,我說只要能付一天就行了,因為這個案子只要花我一天時間。 「一天?」
「沒錯,一天。」我說。
「那科迪怎麼辦?」
「你絕對不會再聽到科迪的消息。」我替她關上車門,她開車走了,碰到第一個紅綠燈時,她停下來朝我揮手道別。
「去字典裡查查『可愛』這個詞,」我們坐在辦公室裡,我對巴巴說,「看看解說旁邊是不是附了凱倫‧尼寇斯的照片。」
巴巴看著我窗台上的那一小堆書。「我怎麼曉得哪本是字典?」
查斯維克接了電話,我告訴他凱倫‧尼寇斯的保險理賠問題。
「沒有遲繳過?」
「從來沒有。」
「沒問題。你剛剛說那是豐田Corolla?」
「沒錯。」
「這什麼車?值兩萬五千元?」
「比較可能是一萬四。」
查斯維克低聲笑了起來。「這麼便宜的車真能跑?」據我所知,查斯維克有一輛賓利(Bentley)、一輛賓士V10,還有兩輛Range Rover。平常他跟一般人見面時,就開一輛凌志(Lexus)。
「他們會付理賠金的。」他說。
「他們原先說不會。」我故意激他。
「那不是要跟我作對嗎?我如果不高興的話,他們就得花五萬元擺平我。他們會付的。」他重複道。
我掛了電話之後,巴巴說,「他說了什麼?」
「他說他們會付的。」
他點點頭。「科迪也會付出代價的,老哥。科迪也會。」
巴巴回他倉庫一下,處理一些雜事;我則打電話給凶殺組的戴文‧安龍克林,他是全波士頓少數還肯跟我講話的警察之一。
「凶殺組。」
「講得真誠一點嘛,寶貝。」
「嘿嘿。誰叫你是波士頓警局天字第一號不受歡迎的人物。最近有沒有被攔車臨檢哪?」
「沒耶。」
「千萬小心別被攔下來。你不會曉得,我們這裡有人想從你後行李廂翻出什麼來。」
我閉上眼睛一會兒。登上警局不爽名單的第一名,可不是我計畫中要達到的人生成就。
「你也不可能太受歡迎,」我說,「你替一個警察同事戴上了手銬。」
「從來沒人喜歡過我。」戴文說,「不過他們大部分都怕我,所以這樣也很好。至於你呢,你可就是個有名望的娘炮了。」
「有名望,嗯?」
「找我有什麼事?」
「我得查一個科迪‧佛克的底,看他以前有沒有跟蹤狂的紀錄。」
「那我能得到什麼回報呢?」
「永恆的友誼?」
「我有個姪女,」他說,「想要整套豆豆公仔當生日禮物。」
「可是你不想去玩具店。」
「另外我有個小孩不肯跟我講話,不過撫養費我還照付,還多得很。」
「所以你也想給這小孩買一套豆豆公仔。」
「一萬應該夠了。」
「一萬?」我說。「你一定是—」
「佛克(Falk),F開頭的嗎?」
「跟騙人(flimflam)的字首一樣。」我說,然後掛了電話。
一個小時後,戴文回電給我,叫我明天晚上把豆豆公仔送到他公寓。
「科迪‧佛克,三十三歲。沒有定罪過。」
「不過呢⋯⋯」
「不過呢,」戴文說,「曾因為違反禁制令接近一位布拉雯‧布萊思而遭到逮捕,起訴撤銷了。曾因為攻擊莎拉‧利托遭到逮捕,然後因為利托小姐拒絕作證又搬到別州,起訴撤銷。曾列為一位安‧伯恩斯坦強暴案的嫌犯,找來警局訊問過,但沒有起訴,因為伯恩斯坦小姐拒絕對起訴書的口供宣誓屬實,拒絕提出強暴驗傷報告,也不願意指認攻擊她的人。」
「真是個大好人哪。」我說。
「聽起來是個小甜甜,沒錯。」
「就這些了嗎?」
「另外他還有未成年犯罪紀錄,不過不能查閱。」
「那當然。」
「他又去騷擾人了嗎?」
「也許吧。」我謹慎地說。
「你小心點。」戴文說,然後掛了電話。 2
科迪‧佛克開的是一輛珍珠灰的奧迪Quattro車,那天晚上九點半,我們看著他開出奧本山俱樂部。他的頭髮剛梳過,還是溼的,運動包裡伸出一支網球拍的拍柄。他穿著柔軟的黑色皮夾克,裡頭是乳白色的亞麻背心,白色襯衫上的釦子扣到喉嚨,下身是褪色的牛仔褲。皮膚曬成很深的古銅色。走起路來一副要人滾開別擋路的氣勢。
「我真的好恨這傢伙。」我跟巴巴說。「可是我根本還不認識他呢。」
「恨一下沒關係,」巴巴說,「又不必花錢。」
科迪用他鑰匙圈上的遙控器解除了防盜設施,那輛奧迪車嗶了兩聲,然後他打開後行李廂。
「如果你肯讓我弄的話,」巴巴說,「他現在就會被炸爛了。」
巴巴本來想在那輛奧迪的引擎體上綁一些C4炸藥,再把引爆線接到奧迪的防盜傳送器上。C4炸藥。可以炸掉半個水城,把奧本山俱樂部給炸到羅德島州去。巴巴不明白這個主意為什麼不好。
「你不能因為他毀掉一個女人的車,就殺了他。」
「是嗎?」巴巴說。「哪裡寫的規定?」
我得承認他考倒我了。
「何況,」巴巴說,「你知道,只要逮到機會,他就會強暴她。」
我點點頭。
「我恨這些潛在的強暴犯。」巴巴說。
「我也是。」
「如果能確保他不會再犯,那就好了。」
我在座位上轉身。「我們不會殺他。」
巴巴聳聳肩。
科迪‧佛克關上他的後行李廂,站在車旁一會兒,強壯的下巴昂起,望著停車場前面的網球場。他看起來像是在擺姿勢,或許是等人給他畫像,而他濃密的深色頭髮、輪廓分明的五官、精心雕琢的軀幹,加上一身柔軟而昂貴的衣服,當模特兒是綽綽有餘。他似乎意識到有人在看他,但不是我們;他好像就是那種人,隨時覺得有人在看他,不是帶著欣賞就是羨慕的眼光。那是科迪‧佛克的世界,主角是他,我們只是住在裡頭的小人物而已。
科迪開出停車場右轉,我們跟著他開過水城,繞過劍橋市的邊緣。他在協和街左轉,駛向貝爾蒙鎮—波士頓時髦貴族郊區中,比較時髦貴族的一個區域。
「為什麼你會把車停在車道上(park in a driveway),可是會開車在林蔭道上(drive on a parkway)?」巴巴握拳遮掉一個哈欠,望著窗外說。
「不曉得。」
「上回我問你,你也是這麼說。」
「然後呢?」
「然後我只是希望有人可以給我個好答案。這問題搞得我很煩。」
我們離開幹道,跟著科迪‧佛克開到一個霧褐色的地帶,沿途有高大的櫟樹和巧克力色的都鐸式建築,夕陽留下了一抹深古銅色的餘暉,為晚冬的街道染上一片秋意;像是鑲著彩繪玻璃、充滿深色柚木和精緻掛毯的私人圖書室,有一種富貴世家的精緻悠閒氣息。
「很高興我們開了保時捷來。」巴巴說。
「你不覺得福特的維多利亞皇冠(Crown Victoria)跟這裡比較配?」
我的保時捷是一輛一九六三年款的Roadster敞篷跑車。十年前我買下來時,幾乎只剩個車殼能用,接下來我花了五年,陸續買零件修復。就這輛車本身而言,我並不喜歡;不過我得承認,每當我坐在方向盤後面,的確感覺自己像是全波士頓最酷的男人。說不定還是全世界最酷的。安琪以前老說這是因為我太不成熟了。安琪說得大概沒錯,不過呢,直到很最近,她開的還是一輛麵包車。
科迪‧佛克駛入一棟巨大的殖民式灰泥建築物旁的小車道,我跟在他後面,等到車庫門呼嚕嚕開始往上捲時,我關掉車前燈。雖然他的車窗都關著,我還是聽得到他車上音響傳來轟然的低音節奏,我們就跟在他後面駛上車道,但他根本沒聽見。我在車門前關掉引擎。他下了那輛奧迪,我們也在車庫門開始降下前下了保時捷。他開了後行李廂,我從車庫門底下走進去,跟他一起待在裡面。
他看到我,往後驚跳,還伸出雙手擋在面前,好像要躲開一大群人似的。然後他開始瞇緊眼睛。我塊頭不是特別大,而科迪精壯又高,還渾身肌肉。他一開始看到自家車庫裡有陌生人的恐懼逐漸消退,轉而打量起我的分量,又看到我沒帶武器。
然後巴巴冒出來。原先科迪車子後行李廂的蓋子擋住他,他伸手給關上,科迪一看猛吸了口氣。巴巴對人就能造成這種效果。他的臉像是發瘋兩年了—彷彿他腦子和良心開始停擺時,五官也跟著柔和且停止成長—臉部底下的那具身軀,老讓我覺得像個鋼製貨車廂長出了手腳。
「媽的這搞什麼—」
巴巴已經從科迪的袋子裡抽出了網球拍,在手中慢慢旋轉著。「為什麼你會把車停在車道上,可是會開車在林蔭道上?」他問科迪。
我看著巴巴,翻了個白眼。
「什麼?媽的我怎麼會曉得?」巴巴聳聳肩。然後他拿網球拍朝奧迪車的後行李廂使勁一揮,在車蓋中央砸出一道大約九吋長的凹痕。 「科迪,」我說,車庫門在後頭轟的一聲剛好關到底,「除非我直接問你問題,否則你半個字都不准出聲,懂了沒?」
他瞪著我。
「剛剛那是個問題,科迪。」
「嗯,是,懂了。」科迪瞥了巴巴一眼,好像整個人縮小了。
巴巴打開網球拍的套子,扔在地上。
「拜託不要再敲車子了。」科迪說。
巴巴輕鬆舉起一手,點點頭,然後流暢地對空反手切球,擊中奧迪車的後車窗。玻璃轟然爆響,碎片落遍科迪車子的後座。
「耶穌啊!」
「剛剛我說你該怎麼講話來著,科迪?」
「可是他剛剛才敲碎我的—」
巴巴扔出那支網球拍,像美洲原住民投擲戰斧那樣,網球拍神準地擊中科迪‧佛克的額頭正中央,讓他整個人往後撞上車庫的牆。他垮在地上,右眉一道口子血流如注,一副快哭出來的表情。
我揪著他的頭髮朝車子一摔,讓他背靠在駕駛座旁的車門坐著。
「你做哪一行的,科迪?」
「我⋯⋯什麼?」
「你的工作是什麼?」
「我是餐館業主。」
「什麼?」巴巴說。
我回頭看了他一眼。「他開餐廳的。」
「喔。」
「哪家餐廳?」
「納罕鎮的船塢餐廳。市中心的旗竿餐廳是我的,崔蒙街燒烤餐廳我有股份,另外還有布魯克萊的四號餐廳。我⋯⋯我—」
「噓,」我說,「你屋裡有人嗎?」
「什麼?」他瘋狂地四處張望。「沒有,沒有。我單身。」
我拉著科迪站起來。「科迪,你喜歡騷擾女人。或許有時還會強暴他們,如果他們不乖乖聽話,就狠狠揍他們,是嗎?」
科迪的雙眼發暗,一滴濃稠的血開始沿著他的鼻樑往下淌。「不,我沒有。誰—」
我手背朝他前額的傷口揮過去,他慘叫。
「安靜點,科迪。安靜點。要是你敢再去煩女人—任何女人—我們就放火燒了你那幾家餐廳,讓你一輩子坐輪椅。聽懂了沒?」
這段關於女人的話,引出了科迪身上的愚蠢。也許是因為我們告訴他,他再也不能以他喜愛的方式擁有女人。無論原因是什麼,他搖搖頭,咬緊牙關。他眼中浮現一種掠食動物的興致,好像他發現了我的致命弱點︰關心「弱勢」的女性。
科迪說,「唔。聽懂了,唔。我不認為我辦得到。」
我退到一邊,巴巴繞到車子這邊,從軍用雨衣的口袋掏出一把點二二口徑的手槍,拴上滅音器,指著科迪‧佛克臉部的正中央,扣下扳機。
作者資料
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
一九六五年八月四日出生於美國麻州多徹斯特,愛爾蘭裔,現居住在波士頓。八歲便立志成為專職作家,出道前為了磨練筆鋒、攥錢維生,曾當過心理諮商師、侍者、代客停車小弟、禮車司機、卡車司機、書店門市人員等,以支持他邁向作家之路的心願。 一九九四年以小說《戰前酒》出道,創造了冷硬男女私探搭檔「派崔克/安琪」系列,黑色幽默的對話與深入家庭、暴力、童年創傷的題材引起書市極大回響,五年內拿下美國推理界夏姆斯、安東尼、巴瑞、戴利斯獎等多項重要大獎,外銷二十多國版權,並以此系列寫下北美一百三十萬、全球兩百四十萬冊的銷售成績。 勒翰真正打入主流文學界,登上巔峰的經典之作是獨立《神祕河流》。小說受好萊塢名導克林伊斯威特青睞改拍成同名電影,獲奧斯卡六項提名,拿下最佳男主角、男配角兩項大獎,小說也因此一舉突破全球兩百五十萬冊的銷售佳績。二○○七年,好萊塢男星班艾佛列克重返編劇行列,取材勒翰的派崔克/安琪系列第四作改拍成同名電影《再見寶貝,再見》(中文片名:失蹤人口),首週便登上北美票房第六名。艾佛列克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勒翰的作品氣氛懸疑、人物紮實,以寫實的筆法書寫城市犯罪與社會邊緣問題,是他將小說改編搬上大銀幕的主要原因,原著小說也隨之攻占紐約時報暢銷小說榜第三名。 二○一○年二月,勒翰另一部暢銷小說《隔離島》也搬上大銀幕,由馬丁史柯西斯執導、李奧納多狄卡皮歐主演,本片是兩人繼《神鬼無間》後再次攜手合作,這也是馬丁史柯西斯首次嘗試驚悚懸疑風格的影劇作品。 近年勒翰投入影視編劇及製片工作,參與作品包括史蒂芬.金小說改編影集《賓士先生》及《局外人》,但也持續在犯罪小說領域創造佳績,以《夜行人生》和《為你沉淪》分別奪得愛倫坡獎、入圍英國犯罪作家金匕首獎。 相關著作:《黑暗,帶我走》
基本資料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