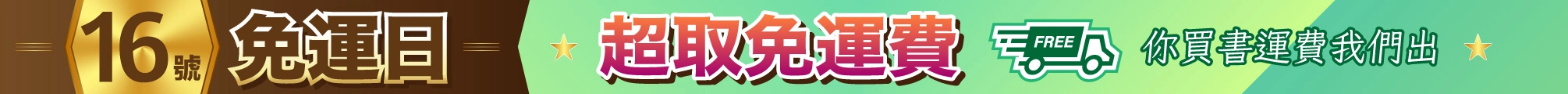分類排行
-
千千萬萬都是你
-
滿分贗品(限)【限量贈品版】
-
重疊愛戀(限)【限量贈品版】
-
風知道的事
-
中場過冬(限量贈品版)【網路超人氣作家妄言熱戀.限制級極致虐心酥慾力作】
-
鬼樂透(文策院影視計畫改編原著全新增修完整版)
-
水魅雷普利【雷普利系列05】(限量附贈海史密斯逝世30週年紀念版「作者親繪貓咪 」書籤):犯罪小說史上最令人不安的經典
-
旅行之木:日本國寶級生態攝影家星野道夫33篇追尋極北大地之夢的旅行手札
-
跟蹤雷普利【雷普利系列04】(限量附贈海史密斯逝世30週年紀念版「作者親繪貓咪 」書籤):犯罪小說史上最令人不安的經典
-
大腦切除師(榮獲諾貝爾獎的「奇蹟器官手術」黑歷史!美國亞馬遜破萬讀者好評,改編自真實事件,揭露醫學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內容簡介
這世上有一本書,不能有名字;
這世上有一個作者,不能告訴別人他是誰;
這一切,就怕惹來殺身之禍……
致親愛的讀者:
這本書只寫給心靈純潔的人看。每一頁、每一章,都引領你一步步接近終點。
並非所有人都能撐到最後,錯綜複雜的情節與文字使人眼花撩亂。而你追尋的真相其實一直都在眼前。黑暗將至,邪惡力量隨之而起。讀了這本書的人,恐怕再也看不見光明。
By 無名氏
【故事簡介】
許多世紀以來,位於南美洲的神祕藏書閣,上頭的書架隱藏著一個可怕的祕密。這個祕密就是有本沒有書名的書,而且出自無名氏的撰寫。每一個看過此書的人紛紛離奇死去,而書本總是會有方法回到這間圖書館。
2005年,特派調查員發現這本書的真相都與謀殺案牽扯在一起。所有讀過書的人都難逃悽慘死狀。
調查員麥爾斯‧詹森被指派到聖塔蒙地迦這個沒有法治的小鎮。這個鎮上看似平常,實際上卻有層出不窮的神祕謀殺事件。每個人都不惜重金以獲得「月之眼」。據說月之眼是一顆美麗的藍色石頭,擁有特殊的力量。但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則一直是個謎,只知道拿到月之眼的人都會招來厄運,莫名其妙的死亡。而隱藏在謀殺案背後的無名之書和月之眼又有什麼關係?
酗酒的連續殺人犯、自認為是貓王的人、一對遺世的僧人,再加上當地黑道頭子、剛從五年昏迷中甦醒的失憶女人、吉卜賽算命師和無助的旅館腳夫。這宗密謀越來越複雜。最重要的是,無名之書在這其中到底扮演什麼關鍵角色?似乎只要讀過這本作者不詳且古老的書,就不能倖免於難。每個讀過的人都被謀殺了。你敢親自解開這個謎底嗎?
【好評推薦】
‧英國亞馬遜4.5顆星評價!
‧閱讀這本書好像騎著正方形輪子的腳踏車狂飆,那是有點奇怪的體驗,但非常有趣!──每日運動報(The Daily Sport)
‧注意!這本書很可能讓你有藥物上癮的異常行為。──Zoo Magazine四顆星評價
‧你得保證你還能維持最專注的注意力,以免再也回不來。──曼徹斯特晚報(Manchester Evening News)
內文試閱
親愛的讀者:
這本書只寫給心靈純潔的人看。
每一頁、每一章,都引領你一步步接近終點。
並非所有人都撐得到最後,錯綜複雜的情節與文字使人眼花撩亂。
而你所追尋的真相其實一直都在眼前。
黑暗將至,邪惡力量隨之而起。
讀了這本書的人,恐怕再也看不見光明。
無名氏
無名氏:「數千年歷史中,許多書籍出自於『無名氏』之手,然而列表整理除了曠日廢時、難以完成,也不知意義何在。」
第一章
桑齊茲不喜歡陌生人進他的店,其實他一樣討厭常客,但是他不得不歡迎他們,因為他害怕他們。想趕走這裡的老主顧等於是自殺,這間西米露酒吧裡頭龍蛇雜處,每個混混都想出頭,想要在道上建立名聲,在這裡逞凶鬥狠就對了。
西米露酒吧是間特別的店,黃色的牆壁,不過不是舒服的黃,而是煙燻的黃。這不是什麼值得訝異的事情,畢竟店裡不成文的規矩就是要會抽菸,不管抽普通捲煙,還是雪茄、菸斗、水煙,就算是大麻也不要緊,只要抽菸都好。不抽菸是不被接受的事。類似的禁忌還有不喝酒,不過最糟糕的是生面孔。生面孔就是壞消息,沒有人相信陌生人。
因此,當那個披著長版黑色斗蓬、撩起風帽的傢伙走進店裡,自顧自地挑了吧台最裡面的座位坐下時,桑齊茲心想的是,他直的進來,恐怕要橫著出去。
店裡大概有二十個熟客在聊天,大夥兒一起閉上了嘴,目光往披著帽子的人掃過去。桑齊茲還注意到他們停手不碰酒了,這不是好現象,如果店裡放著音樂,大概在那陌生男子出現的同時也會停下來吧,只剩天花板上吊扇轉動的聲音。
桑齊茲假裝沒看見客人進來,但那人一旦開口,他也很難繼續演戲。
「老闆,給我杯波本。」
陌生男子沒抬頭,連正眼也不瞧桑齊茲就這麼點了酒,加上風帽蓋住臉,沒辦法知道他的長相是不是跟聲音一樣討人厭。這不速之客的聲音充滿顆粒,倒出來可以裝滿一個杯子吧(生面孔惹不惹人厭,通常就是用聲音裡有多少顆粒來判斷)。桑齊茲心裡盤算一下,拿了個看來頗乾淨的威士忌酒杯,走到那男人座位前面。他把酒杯擱在黏搭搭的木頭吧台上,趁機朝著黑色風帽底下瞥一眼,可惜帽沿影子太重,他沒看清楚那人的五官,當然他也不想冒著被抓到一直盯著看的風險。
「加冰。」那男人又低聲冒出一句話,聽起來像呼氣一樣輕,但聲音同樣帶著一大團沙礫。
桑齊茲從吧台底下取出一支酒瓶,裡面有半瓶棕色的液體,外瓶標籤寫著「波本」,接著另一手夾了兩顆冰塊、扔進杯裡,他倒了半杯,又把酒瓶給收回吧台底下。
「三塊錢。」
「要三元?」
「對。」
「裝滿。」
打從這人進店裡來就一直鴉雀無聲,現在更是靜得跟墳場一樣,唯一例外的還是吊扇,轉動聲好像愈來愈大。這時桑齊茲的眼神不敢跟任何人交會,他又拿出酒瓶,灌滿杯子,陌生男子丟了張五元鈔票在吧台上。
「剩下的當小費。」
桑齊茲轉身操作收銀機,卻忽然有人開口打斷這陣叮叮咚咚的聲響,林戈的聲音從背後冒出來。他是桑齊茲這兒最難纏的客人之一,說起話來也是含著一大把沙子。
「外地人,你到咱們這間店來幹嘛?」
林戈跟兩個朋友坐在一起,距離陌生人後頭幾公尺而已。他是個又高又重、滿面油光與鬍渣的惡漢,就和這間酒吧裡的其他人一個樣。林戈的腰上掛著槍,渴望出現任何讓他亮槍的理由。桑齊茲站在收銀機前面,深呼吸,準備好等著接下來不可避免要發生的事。
林戈是出了名的亡命之徒,任何想得到的罪名他都有份。強暴、謀殺、縱火、竊盜、殺警察,如你所見,林戈全都坦承犯案,要是哪一天他沒做什麼不法的事,才真的該入獄。今天也沒什麼不一樣。林戈剛用這把槍搶了三個人,現在這筆來路不正的錢全花在啤酒上。而他正伺機挑起任何可能的衝突。
一回頭,他看見那陌生人動也不動,而且沒伸手拿酒。幾秒鐘過去,他沒有回答林戈的問題;桑齊茲還記得親眼看過林戈射傷別人的膝蓋,只因為對方沒有立刻回話。林戈問了第二次,那男人終於開口,他鬆了一口氣。
「我不是來找麻煩的。」
林戈不懷好意冷笑起來,惡狠狠地接口:「我就是麻煩,你已經找到我了。」 披著風帽的男子沒回應,只是坐在板凳上,眼睛望著酒杯。林戈站起來走到陌生人旁邊,身體靠著吧台,一揮手就拉下風帽,露出一張輪廓深邃但不修邊幅的面孔,看上去是個三十多歲的金髮男子,眼睛帶著血絲,彷彿昨夜宿醉,或者只是喝多了卻沒睡飽。
「我要知道你到底來幹嘛的,」林戈追問:「聽說有個外地人一大早到我們這兒來囂張,該不會就是你吧?」
「我不囂張。」
「那你就穿好衣服給我滾出去。」
嚴格來說,那外地人根本沒脫下衣服。
金髮男子聽了林戈的話,思考了一會兒,然後搖頭。「我知道你說的外地人是誰,」他用嘶啞的聲音回答:「我還知道他為什麼來到這裡,如果你不找碴,我可以告訴你他的來歷。」
林戈又濃又髒的鬍子底下漾起冷笑,他回頭掃過酒吧裡的聽眾一眼,二十來個熟面孔坐著看戲。他臉上的笑意看似緩和了尷尬氣氛,但大家心裡都明白這氣氛只會再度回到冰點,西米露酒吧可不是什麼好混的地方。
「大夥兒覺得如何?我們要不要聽這帥哥講故事?」
撞杯聲此起彼落,很多人叫好,林戈伸手朝金髮男子一搭,把他轉過來面對大家。
「那麼帥哥,跟大家說說那混帳東西的事情好了,他跑來我們鎮上做什麼?」
林戈語氣裡的嘲笑意味再清楚不過,但那金髮男人好似也不在意,就這麼接了下去。
「今天早上我順著路走,幾哩之後進了間酒館,後來有個很高很壯、看起來不好惹的傢伙也進去了,他坐在吧台點了一杯酒。」
「這傢伙長什麼樣子?」
「他披著一個大風帽,所以看不見臉,但是後來有個白目過去掀了他帽子。」
林戈聽了笑不下去,懷疑這傢伙揶揄他,他靠上去抓緊對方肩膀。
「告訴我,小子,接下來怎麼啦?」他語帶恫嚇。
「結果那外地人其實長得還蠻帥的,酒一口喝光,掏出手槍殺光了酒吧裡的人……只留下我跟酒保而已。」
「喔?」林戈鼓起髒兮兮的鼻孔深深吸了一口氣:「我懂為什麼他不殺酒保,但我想不通為什麼不連你一起宰掉呢?」
「你想知道他為什麼不殺我啊?」
林戈從寬版皮帶上甩出了槍,朝那男人臉上一指,差點戳在他臉上。
「對,我想知道那王八蛋為什麼不殺你。」
外地人無視左輪槍,眼睛朝林戈一望。「嗯哼,」他回答:「他不殺我,因為他要我到這間爛店找頭叫林戈的蠢豬。」
特別強調的最後兩字,林戈也聽得出來,但在大家的震驚中,他倒是心平氣和地繼續問下去,至少以他的標準來說算是很冷靜了。
「我就是林戈,你他媽的又是哪根蔥?」
「這不重要。」
跟林戈同桌的兩個小混混站起來,朝吧台跨出一步,隨時打算支援。
「我覺得很重要,」林戈磨著牙:「我們聽說那個外地人自稱是『波本小子』,你點的也是波本沒錯吧?」
金髮男子看了看林戈身後兩個鄉巴佬,又看了看林戈的槍管。
「那你知道他為什麼有這外號嗎?」
「我聽說,」林戈的朋友在他背後開口:「聽說『波本小子』喝了波本威士忌,就會變成殺人不眨眼的巨人,會殺光眼前所有的人,還有他天下無敵,只有撒旦才收拾得了他。」
「沒錯,」金髮男子接了下去:「『波本小子』會殺光所有人,只要喝杯酒他就會發狂,據說波本威士忌可以給他神奇的力量,喝完一口就會殺光酒吧裡的地痞。我相信,因為我親眼看過了。」
林戈的槍口對準他的太陽穴:「喝你的波本。」
金髮男子的身體轉了轉,又面對吧台,伸手端起酒杯。林戈跟著他的動作,槍口始終瞄準他腦袋。
站在吧台裡面的桑齊茲一直往外退,他可不希望沾到濺出來的血或腦漿,更擔心會被流彈打中。他看著金髮男子拿起酒杯,正常人在這情況下多少要發抖,灑了半杯都不奇怪,但這外地人卻跟杯子裡的冰塊一樣冷靜,這點倒是令人敬佩。 西米露酒吧裡的所有客人都站起來觀望,看看到底怎麼回事,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的手都搭在槍上。大家看著這陌生人端著杯子在面前晃呀晃,似乎是研究裡頭裝著什麼,玻璃杯外面有一滴水珠,看樣子是汗,也許是桑齊茲的手汗,也許是前一個客人的汗,總之那金髮男子好像也就看著那滴汗,一直等著汗珠滑落,似乎是等到他的舌頭不用沾到汗水。終於那水珠滑到他嘴巴碰不到的地方,他吸了一口氣,將杯中物全灌進嘴裡。
三秒鐘左右,杯子就空了,整間酒館的人屏息以待,但沒有任何變化。
大家不敢呼吸繼續等。
還是沒有任何變化。
大家只好換一口氣,吊扇好像重新轉動起來。
還是沒變化。
林戈從那人臉上移開槍,問了埋在每個人心中的疑惑:「所以你到底是不是『波本小子』?」
「喝掉剛剛那杯尿,只能證明一件事。」金髮男子用手背抹過嘴。
「喔?證明什麼事?」
「原來我喝尿也不會吐。」
林戈朝桑齊茲看過去,桑齊茲早就閃到最遠的角落,背靠著牆壁,看上去在發抖。
「你剛剛拿的是尿?」林戈問道。
桑齊茲不太自在但點了點頭:「我覺得他看上去怪怪的哪。」
林戈把槍收回腰帶,走了開,忽然又回頭狂笑,還拍了拍那外地人肩膀。
「你喝了一整杯尿!哈哈哈……一整杯耶!你居然喝光一杯尿!」
店裡頭每個人都跟著笑了,金髮男子例外,他只是直直瞪著桑齊茲。
「他媽的給我杯波本威士忌。」他聲音裡的顆粒更大了。
桑齊茲轉身拿了另外一罐貼有波本標籤的瓶子出來,倒在外地人的酒杯裡,沒等對方開口就主動倒滿。
「三塊錢。」
任誰也看得出來,那外地人對於桑齊茲還有膽再收三元相當不爽,而且這不爽已經滿到臉上。他的動作快到來不及看清楚,右手已經從黑斗蓬裡拔出一把槍,槍身灰灰的、看上去份量很重,應該是裝滿子彈。原本槍管可能是閃亮的銀色,但西米露酒吧的人再清楚不過:如果手槍光潔如新,那很可能真的沒用過。這個人手槍很舊,代表他可能開過很多槍。
他行雲流水地直接瞄準了桑齊茲額頭,等到大家發現他有動作,立刻傳來二十多下左輪手槍拉保險的喀擦聲。早在每個人都靜下來觀望的時候,就已經掏出手槍對準那外地人。
「帥哥,你冷靜點。」林戈也一樣,槍口又對準了他的太陽穴。
桑齊茲慌張之中帶著歉意朝外地人苦笑,但那外地人的手槍可沒有移開。
「這杯算店裡招待的吧……」酒保連忙說。
「我也不像想付錢的樣子吧?」金髮男子簡單答道。
後來大家都沒說話,金髮男子將手槍擱在杯子旁邊,輕輕嘆口氣。他看上去很火大,極需一杯飲料消消氣,味道正常的酒才能洗掉他口中的尿臊味。
他拿了酒杯朝嘴邊一送,整間酒吧的人凝神注視,聚精會神想知道他喝了酒會發生什麼事。但他不知道是不是刻意要吊人胃口,不肯像剛剛一口氣全吞下,等了半天一副想開口講話的模樣,搞得其他客人都喘不過氣。他要說什麼?他到底要不要喝酒?
但也沒有等太久,金髮男子彷彿一整星期沒喝到酒,一張嘴就喝光了杯中的威士忌,然後杯子在吧台上重重一敲。
這次是真正的「波本」威士忌。 第二章
陶斯長老很想哭。他這輩子有過不少悲傷的時刻,可能一兩天,可能一兩星期,也不是沒有過整個月都沉浸在悲傷中的經驗,但現在是他最痛苦的一次,也許會是他一生之中最悲痛的時刻了。
他一如往常站在赫瑞瑞神殿的祭壇高台上,望著底下一排排座位,可惜今天看見的景象不一樣,座位上不是他想看見的東西。以前至少有一半坐著表情死板的人,那是跟他一樣,信奉胡巴爾(譯註)的弟兄們。也有時候,椅子上一個人都沒有,陶斯長老就算望著空位也覺得整齊乾淨,淡紫色椅墊令人心曠神怡。但今天看到的不是這樣,底下的座位不乾淨,也非紫色,弟兄們看上去也不死板。
※譯註:胡巴爾(Hubal)是阿拉伯地方信奉回教之前崇拜的月神,為信仰中的主神,後來穆罕默德則將胡巴爾與阿拉同化。
空氣中的味道如此陌生,陶斯長老以前只聞過一次,那是五年前的事情了,這段回憶令他作嘔,那代表了死亡、毀滅、背叛,上頭還覆蓋著火藥味。椅墊不再是淡紫,上頭都是血,看上去不可能乾淨整齊,根本就是人間煉獄,確實在一半的位置上找得到胡巴爾教的弟兄,但他們的表情不能稱為死板,就是死了而已,全死了。
陶斯長老抬頭往上看,在五十呎高的地方,有血從天花板墜落。這兒的大理石拱頂弧度相當精美,幾百年前就畫上了聖天使與孩童一同歡笑舞蹈的美妙光景,可是如今天使與孩子也沾上了教士的血,彷彿表情也變了,沒辦法快樂自在,帶著血跡的臉上露出哀痛與不安,跟陶斯長老如出一轍。
三十幾具屍體倒在座位上,看不見的、滑到椅子底下的大概還有三十幾具,大屠殺後只有一個人活下來,那就是陶斯長老。有人近距離對準他的腹部開槍,雙管散彈槍,很痛。傷口到現在還在出血,但會癒合的,他所受的傷都會癒合;槍傷癒合後還是有疤痕,但他也習慣了。陶斯從前有過兩次槍傷,也是五年前的事情,同一個星期裡,相距不過幾天。
島上胡巴爾信眾夠多,沒死的人可以幫忙清理這團混亂,但他知道對大夥兒來說,這是很痛苦的事情,對那些經歷過五年前事件的人更是如此,上次也一樣,神殿的莊嚴氣氛在瀰漫的火藥味中蕩然無存。也因此,陶斯長老看見進來的兩個人覺得寬心不少,那是兩個比較年輕的教士,一個是凱爾,另一個是彼多,他們穿過大洞走進來,那裡原本是兩扇壯觀的橡木拱門。
凱爾大概三十歲,彼多只有二十左右,但很多人第一眼會誤以為這兩人是雙胞胎,他們不只外表相仿,連氣質也接近。一方面他們穿著一模一樣,另一方面,將近十年來,凱爾可謂是彼多的精神導師,彼多下意識模仿凱爾銳利而謹慎的性格。兩個人都皮膚黝黑、留著平頭,套著一模一樣的棕色袍子,斷氣的那些教士也是。
兩個年輕教士要上祭壇察看陶斯長老的傷勢,但得先咬牙穿過一干弟兄的遺體才到得了。陶斯看著他們的困窘心裡難過,但只要看見他們就已安心一些,暖意湧上心頭,心跳也快了。前一小時裡,他一分鐘脈搏只有十下,對他來說心臟動得快一點、穩定下來是好事。
彼多還細心,拿了陶杯裝水給陶斯長老喝,前往祭壇的路上他注意著不讓水灑出來,但雙手還是不停顫抖,可見神殿裡的情景強烈衝擊他。他遞水給陶斯長老,不僅陶斯鬆口氣,彼多自己也是。長老兩手捧著壺,用剩下的力氣湊到嘴邊,沁涼泉水滑進喉嚨使他彷彿重獲新生,對於身體的痊癒也大有幫助。
「謝謝你,彼多。你不用擔心,不用到明天,我這把老骨頭就能回復。」陶斯一邊說一邊將杯子擱在地上。
「我相信長老會好起來的。」彼多說話也在抖,不像是很有信心,但至少還懷著一絲希望。
這是陶斯今天第一次露出笑容。彼多好純真、好體貼,他就身在這座喋血神殿裡面,也能夠令人相信事情都會好轉。十歲的時候,彼多雙親慘死在毒販手裡,他就被送到這座島上,與教士一同生活以後,他找到內心的平靜與勇氣,終於放下喪親之痛好好生活。看見彼多長大成人,而且這樣善良、仁慈、無私,陶斯一直為自己、為所有弟兄感到驕傲。天不從人願,現在他可得將這孩子送回當年剝奪他天倫之樂的世界去。
「凱爾、彼多,你們應該都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過來吧。」
「是,長老。」凱爾代表兩人回答。
「那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長老。如果長老覺得我們沒準備好,也不會叫我們過來了吧。」
「沒錯,凱爾。你果然思路清晰,我常忘記這點。彼多你別錯過,多跟凱爾學學。」
「我會的,長老。」彼多謙卑地回答。
「接下來我說的事情你們要聽好。時間不多了……」陶斯繼續說:「此刻起,每秒鐘都彌足珍貴,自由世界的延續或存在與否,已經成為你們肩膀上的重擔。」
「我們不會令長老,失望。」凱爾很肯定地回答最後兩個字。 「只是針對我的話,失望也無所謂。但是凱爾,這件工作沒辦妥,是全人類要失望……」陶斯頓了一下又重新開口:「找出石頭的下落,帶回這座神殿。黑暗降臨之時,石頭絕不可以落入惡人之手。」
「這是什麼意思?」彼多問:「長老,之後會怎麼樣?」
陶斯伸手搭在彼多肩上,以他現在的體能而言,是很大的力道。陶斯受到腥風血雨所震撼,也害怕即將到來的威脅,更重要的是他深感無力,除了派這兩個年輕人出去,居然沒有其他辦法了。
「你們兩個聽好,石頭落入有心人手中,時機一到,我們也躲不過了。到時候巨浪滔天,人類會像大雨中的淚水一樣全被沖走。」
「大雨中的淚水?」彼多重複了一次這段話。
「沒錯,彼多。」陶斯長老輕聲回答:「大雨中的淚水……你們得趕快出發,沒時間多解釋了,要立刻開始行動,每分每秒我們都更靠近世界末日,我們所知所愛的世界有危險。」
凱爾伸手輕碰長老的臉,替他抹去一道血漬。
「長老請別擔心,我們不會遲疑。」話雖如此,他還是猶豫了一陣,然後開口問:「但我們要從哪裡開始找?」
「孩子,一樣的地方。去聖塔蒙地迦,那裡有人想得到『月之眼』,一定是帶到那兒去。」
「但是……『有人』是說誰呢?是誰下的毒手?我們要找的是誰、還是什麼東西?」
陶斯長老停頓一會兒沒回答,看了看身邊慘況,想到自己曾經與凶手四目相交,接著對方朝他開了槍。
「凱爾,去找一個人,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你們在聖塔蒙地迦一帶打聽打聽,問問是不是有個殺不死的人,或者找到一個能單槍匹馬、完全不受傷就殺死三、四十個對手的人。」
「長老,如果真有這樣一個人,鎮上居民敢跟我們透露太多嗎?」
陶斯對這年輕人一連串的問題不耐,然而凱爾說的沒錯,他思考著。凱爾有個優點:他如果提出疑問,至少都是真的想過。這一次,陶斯還有辦法回答。
「你講的有道理,可是聖塔蒙地迦不一樣,那是個靠口袋裡東西辦事的地方……」
「口袋裡的東西?」
「錢哪,凱爾。外面世界的人,為了錢什麼事情都肯幹。」
「但是我們沒有錢吧?根據胡巴爾的律法,我們不使用金錢……」
「技術上來說是如此,」陶斯說:「不過其實我們有錢,不用而已。去碼頭找山謬弟兄,他會給你們一口箱子,裡面滿滿的都是錢,遠超過一個人一輩子所需。你們用這筆資金,在那邊收集情報吧。」說到這邊,陶斯覺得疲憊,還感受到巨大的悲慟,伸手摀住臉才能繼續往下說:「沒有錢的話,你們在聖塔蒙地迦撐不過一天吧,記住……不管你們想怎麼做,錢絕對不可以離身,行事謹慎、財別露白,不然引人覬覦,外頭壞人很多。」
「瞭解了,長老。」
凱爾心裡頭覺得刺激,他小時候就來到島上,這是第一次可以到外界走走。胡巴爾教士都是嬰兒時期到這座島,有些人是孤兒、有些人是父母棄養,成為教士後,一輩子都不一定有機會出去。只不過身為胡巴爾教士,凱爾對於自己居然期待旅行而生出強烈罪惡感,此時此景不能這樣想。
「長老還有要交代的事情嗎?」他問。
陶斯搖搖頭。「沒有了,孩子,出發吧。你們有三天時間可以奪回月之眼,以阻止世界滅亡,已經開始倒數計時了。」
凱爾與彼多對長老鞠躬行禮,轉身,戒慎恐懼地步出神殿。他們其實急著去外頭換換氣,神殿裡面滿溢的死亡氣息令人作嘔。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一旦離開這座島,只會愈來愈熟悉這個的味道。陶斯長老明白這一點,看著兩個年輕人離去,他真希望自己有勇氣可以說出外面世界的真實樣貌。五年前,他派了兩個年輕教士到聖塔蒙地迦,然而那兩人沒有回來,知道原因的只有陶斯一人。
這本書只寫給心靈純潔的人看。
每一頁、每一章,都引領你一步步接近終點。
並非所有人都撐得到最後,錯綜複雜的情節與文字使人眼花撩亂。
而你所追尋的真相其實一直都在眼前。
黑暗將至,邪惡力量隨之而起。
讀了這本書的人,恐怕再也看不見光明。
無名氏
無名氏:「數千年歷史中,許多書籍出自於『無名氏』之手,然而列表整理除了曠日廢時、難以完成,也不知意義何在。」
第一章
桑齊茲不喜歡陌生人進他的店,其實他一樣討厭常客,但是他不得不歡迎他們,因為他害怕他們。想趕走這裡的老主顧等於是自殺,這間西米露酒吧裡頭龍蛇雜處,每個混混都想出頭,想要在道上建立名聲,在這裡逞凶鬥狠就對了。
西米露酒吧是間特別的店,黃色的牆壁,不過不是舒服的黃,而是煙燻的黃。這不是什麼值得訝異的事情,畢竟店裡不成文的規矩就是要會抽菸,不管抽普通捲煙,還是雪茄、菸斗、水煙,就算是大麻也不要緊,只要抽菸都好。不抽菸是不被接受的事。類似的禁忌還有不喝酒,不過最糟糕的是生面孔。生面孔就是壞消息,沒有人相信陌生人。
因此,當那個披著長版黑色斗蓬、撩起風帽的傢伙走進店裡,自顧自地挑了吧台最裡面的座位坐下時,桑齊茲心想的是,他直的進來,恐怕要橫著出去。
店裡大概有二十個熟客在聊天,大夥兒一起閉上了嘴,目光往披著帽子的人掃過去。桑齊茲還注意到他們停手不碰酒了,這不是好現象,如果店裡放著音樂,大概在那陌生男子出現的同時也會停下來吧,只剩天花板上吊扇轉動的聲音。
桑齊茲假裝沒看見客人進來,但那人一旦開口,他也很難繼續演戲。
「老闆,給我杯波本。」
陌生男子沒抬頭,連正眼也不瞧桑齊茲就這麼點了酒,加上風帽蓋住臉,沒辦法知道他的長相是不是跟聲音一樣討人厭。這不速之客的聲音充滿顆粒,倒出來可以裝滿一個杯子吧(生面孔惹不惹人厭,通常就是用聲音裡有多少顆粒來判斷)。桑齊茲心裡盤算一下,拿了個看來頗乾淨的威士忌酒杯,走到那男人座位前面。他把酒杯擱在黏搭搭的木頭吧台上,趁機朝著黑色風帽底下瞥一眼,可惜帽沿影子太重,他沒看清楚那人的五官,當然他也不想冒著被抓到一直盯著看的風險。
「加冰。」那男人又低聲冒出一句話,聽起來像呼氣一樣輕,但聲音同樣帶著一大團沙礫。
桑齊茲從吧台底下取出一支酒瓶,裡面有半瓶棕色的液體,外瓶標籤寫著「波本」,接著另一手夾了兩顆冰塊、扔進杯裡,他倒了半杯,又把酒瓶給收回吧台底下。
「三塊錢。」
「要三元?」
「對。」
「裝滿。」
打從這人進店裡來就一直鴉雀無聲,現在更是靜得跟墳場一樣,唯一例外的還是吊扇,轉動聲好像愈來愈大。這時桑齊茲的眼神不敢跟任何人交會,他又拿出酒瓶,灌滿杯子,陌生男子丟了張五元鈔票在吧台上。
「剩下的當小費。」
桑齊茲轉身操作收銀機,卻忽然有人開口打斷這陣叮叮咚咚的聲響,林戈的聲音從背後冒出來。他是桑齊茲這兒最難纏的客人之一,說起話來也是含著一大把沙子。
「外地人,你到咱們這間店來幹嘛?」
林戈跟兩個朋友坐在一起,距離陌生人後頭幾公尺而已。他是個又高又重、滿面油光與鬍渣的惡漢,就和這間酒吧裡的其他人一個樣。林戈的腰上掛著槍,渴望出現任何讓他亮槍的理由。桑齊茲站在收銀機前面,深呼吸,準備好等著接下來不可避免要發生的事。
林戈是出了名的亡命之徒,任何想得到的罪名他都有份。強暴、謀殺、縱火、竊盜、殺警察,如你所見,林戈全都坦承犯案,要是哪一天他沒做什麼不法的事,才真的該入獄。今天也沒什麼不一樣。林戈剛用這把槍搶了三個人,現在這筆來路不正的錢全花在啤酒上。而他正伺機挑起任何可能的衝突。
一回頭,他看見那陌生人動也不動,而且沒伸手拿酒。幾秒鐘過去,他沒有回答林戈的問題;桑齊茲還記得親眼看過林戈射傷別人的膝蓋,只因為對方沒有立刻回話。林戈問了第二次,那男人終於開口,他鬆了一口氣。
「我不是來找麻煩的。」
林戈不懷好意冷笑起來,惡狠狠地接口:「我就是麻煩,你已經找到我了。」 披著風帽的男子沒回應,只是坐在板凳上,眼睛望著酒杯。林戈站起來走到陌生人旁邊,身體靠著吧台,一揮手就拉下風帽,露出一張輪廓深邃但不修邊幅的面孔,看上去是個三十多歲的金髮男子,眼睛帶著血絲,彷彿昨夜宿醉,或者只是喝多了卻沒睡飽。
「我要知道你到底來幹嘛的,」林戈追問:「聽說有個外地人一大早到我們這兒來囂張,該不會就是你吧?」
「我不囂張。」
「那你就穿好衣服給我滾出去。」
嚴格來說,那外地人根本沒脫下衣服。
金髮男子聽了林戈的話,思考了一會兒,然後搖頭。「我知道你說的外地人是誰,」他用嘶啞的聲音回答:「我還知道他為什麼來到這裡,如果你不找碴,我可以告訴你他的來歷。」
林戈又濃又髒的鬍子底下漾起冷笑,他回頭掃過酒吧裡的聽眾一眼,二十來個熟面孔坐著看戲。他臉上的笑意看似緩和了尷尬氣氛,但大家心裡都明白這氣氛只會再度回到冰點,西米露酒吧可不是什麼好混的地方。
「大夥兒覺得如何?我們要不要聽這帥哥講故事?」
撞杯聲此起彼落,很多人叫好,林戈伸手朝金髮男子一搭,把他轉過來面對大家。
「那麼帥哥,跟大家說說那混帳東西的事情好了,他跑來我們鎮上做什麼?」
林戈語氣裡的嘲笑意味再清楚不過,但那金髮男人好似也不在意,就這麼接了下去。
「今天早上我順著路走,幾哩之後進了間酒館,後來有個很高很壯、看起來不好惹的傢伙也進去了,他坐在吧台點了一杯酒。」
「這傢伙長什麼樣子?」
「他披著一個大風帽,所以看不見臉,但是後來有個白目過去掀了他帽子。」
林戈聽了笑不下去,懷疑這傢伙揶揄他,他靠上去抓緊對方肩膀。
「告訴我,小子,接下來怎麼啦?」他語帶恫嚇。
「結果那外地人其實長得還蠻帥的,酒一口喝光,掏出手槍殺光了酒吧裡的人……只留下我跟酒保而已。」
「喔?」林戈鼓起髒兮兮的鼻孔深深吸了一口氣:「我懂為什麼他不殺酒保,但我想不通為什麼不連你一起宰掉呢?」
「你想知道他為什麼不殺我啊?」
林戈從寬版皮帶上甩出了槍,朝那男人臉上一指,差點戳在他臉上。
「對,我想知道那王八蛋為什麼不殺你。」
外地人無視左輪槍,眼睛朝林戈一望。「嗯哼,」他回答:「他不殺我,因為他要我到這間爛店找頭叫林戈的蠢豬。」
特別強調的最後兩字,林戈也聽得出來,但在大家的震驚中,他倒是心平氣和地繼續問下去,至少以他的標準來說算是很冷靜了。
「我就是林戈,你他媽的又是哪根蔥?」
「這不重要。」
跟林戈同桌的兩個小混混站起來,朝吧台跨出一步,隨時打算支援。
「我覺得很重要,」林戈磨著牙:「我們聽說那個外地人自稱是『波本小子』,你點的也是波本沒錯吧?」
金髮男子看了看林戈身後兩個鄉巴佬,又看了看林戈的槍管。
「那你知道他為什麼有這外號嗎?」
「我聽說,」林戈的朋友在他背後開口:「聽說『波本小子』喝了波本威士忌,就會變成殺人不眨眼的巨人,會殺光眼前所有的人,還有他天下無敵,只有撒旦才收拾得了他。」
「沒錯,」金髮男子接了下去:「『波本小子』會殺光所有人,只要喝杯酒他就會發狂,據說波本威士忌可以給他神奇的力量,喝完一口就會殺光酒吧裡的地痞。我相信,因為我親眼看過了。」
林戈的槍口對準他的太陽穴:「喝你的波本。」
金髮男子的身體轉了轉,又面對吧台,伸手端起酒杯。林戈跟著他的動作,槍口始終瞄準他腦袋。
站在吧台裡面的桑齊茲一直往外退,他可不希望沾到濺出來的血或腦漿,更擔心會被流彈打中。他看著金髮男子拿起酒杯,正常人在這情況下多少要發抖,灑了半杯都不奇怪,但這外地人卻跟杯子裡的冰塊一樣冷靜,這點倒是令人敬佩。 西米露酒吧裡的所有客人都站起來觀望,看看到底怎麼回事,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的手都搭在槍上。大家看著這陌生人端著杯子在面前晃呀晃,似乎是研究裡頭裝著什麼,玻璃杯外面有一滴水珠,看樣子是汗,也許是桑齊茲的手汗,也許是前一個客人的汗,總之那金髮男子好像也就看著那滴汗,一直等著汗珠滑落,似乎是等到他的舌頭不用沾到汗水。終於那水珠滑到他嘴巴碰不到的地方,他吸了一口氣,將杯中物全灌進嘴裡。
三秒鐘左右,杯子就空了,整間酒館的人屏息以待,但沒有任何變化。
大家不敢呼吸繼續等。
還是沒有任何變化。
大家只好換一口氣,吊扇好像重新轉動起來。
還是沒變化。
林戈從那人臉上移開槍,問了埋在每個人心中的疑惑:「所以你到底是不是『波本小子』?」
「喝掉剛剛那杯尿,只能證明一件事。」金髮男子用手背抹過嘴。
「喔?證明什麼事?」
「原來我喝尿也不會吐。」
林戈朝桑齊茲看過去,桑齊茲早就閃到最遠的角落,背靠著牆壁,看上去在發抖。
「你剛剛拿的是尿?」林戈問道。
桑齊茲不太自在但點了點頭:「我覺得他看上去怪怪的哪。」
林戈把槍收回腰帶,走了開,忽然又回頭狂笑,還拍了拍那外地人肩膀。
「你喝了一整杯尿!哈哈哈……一整杯耶!你居然喝光一杯尿!」
店裡頭每個人都跟著笑了,金髮男子例外,他只是直直瞪著桑齊茲。
「他媽的給我杯波本威士忌。」他聲音裡的顆粒更大了。
桑齊茲轉身拿了另外一罐貼有波本標籤的瓶子出來,倒在外地人的酒杯裡,沒等對方開口就主動倒滿。
「三塊錢。」
任誰也看得出來,那外地人對於桑齊茲還有膽再收三元相當不爽,而且這不爽已經滿到臉上。他的動作快到來不及看清楚,右手已經從黑斗蓬裡拔出一把槍,槍身灰灰的、看上去份量很重,應該是裝滿子彈。原本槍管可能是閃亮的銀色,但西米露酒吧的人再清楚不過:如果手槍光潔如新,那很可能真的沒用過。這個人手槍很舊,代表他可能開過很多槍。
他行雲流水地直接瞄準了桑齊茲額頭,等到大家發現他有動作,立刻傳來二十多下左輪手槍拉保險的喀擦聲。早在每個人都靜下來觀望的時候,就已經掏出手槍對準那外地人。
「帥哥,你冷靜點。」林戈也一樣,槍口又對準了他的太陽穴。
桑齊茲慌張之中帶著歉意朝外地人苦笑,但那外地人的手槍可沒有移開。
「這杯算店裡招待的吧……」酒保連忙說。
「我也不像想付錢的樣子吧?」金髮男子簡單答道。
後來大家都沒說話,金髮男子將手槍擱在杯子旁邊,輕輕嘆口氣。他看上去很火大,極需一杯飲料消消氣,味道正常的酒才能洗掉他口中的尿臊味。
他拿了酒杯朝嘴邊一送,整間酒吧的人凝神注視,聚精會神想知道他喝了酒會發生什麼事。但他不知道是不是刻意要吊人胃口,不肯像剛剛一口氣全吞下,等了半天一副想開口講話的模樣,搞得其他客人都喘不過氣。他要說什麼?他到底要不要喝酒?
但也沒有等太久,金髮男子彷彿一整星期沒喝到酒,一張嘴就喝光了杯中的威士忌,然後杯子在吧台上重重一敲。
這次是真正的「波本」威士忌。 第二章
陶斯長老很想哭。他這輩子有過不少悲傷的時刻,可能一兩天,可能一兩星期,也不是沒有過整個月都沉浸在悲傷中的經驗,但現在是他最痛苦的一次,也許會是他一生之中最悲痛的時刻了。
他一如往常站在赫瑞瑞神殿的祭壇高台上,望著底下一排排座位,可惜今天看見的景象不一樣,座位上不是他想看見的東西。以前至少有一半坐著表情死板的人,那是跟他一樣,信奉胡巴爾(譯註)的弟兄們。也有時候,椅子上一個人都沒有,陶斯長老就算望著空位也覺得整齊乾淨,淡紫色椅墊令人心曠神怡。但今天看到的不是這樣,底下的座位不乾淨,也非紫色,弟兄們看上去也不死板。
※譯註:胡巴爾(Hubal)是阿拉伯地方信奉回教之前崇拜的月神,為信仰中的主神,後來穆罕默德則將胡巴爾與阿拉同化。
空氣中的味道如此陌生,陶斯長老以前只聞過一次,那是五年前的事情了,這段回憶令他作嘔,那代表了死亡、毀滅、背叛,上頭還覆蓋著火藥味。椅墊不再是淡紫,上頭都是血,看上去不可能乾淨整齊,根本就是人間煉獄,確實在一半的位置上找得到胡巴爾教的弟兄,但他們的表情不能稱為死板,就是死了而已,全死了。
陶斯長老抬頭往上看,在五十呎高的地方,有血從天花板墜落。這兒的大理石拱頂弧度相當精美,幾百年前就畫上了聖天使與孩童一同歡笑舞蹈的美妙光景,可是如今天使與孩子也沾上了教士的血,彷彿表情也變了,沒辦法快樂自在,帶著血跡的臉上露出哀痛與不安,跟陶斯長老如出一轍。
三十幾具屍體倒在座位上,看不見的、滑到椅子底下的大概還有三十幾具,大屠殺後只有一個人活下來,那就是陶斯長老。有人近距離對準他的腹部開槍,雙管散彈槍,很痛。傷口到現在還在出血,但會癒合的,他所受的傷都會癒合;槍傷癒合後還是有疤痕,但他也習慣了。陶斯從前有過兩次槍傷,也是五年前的事情,同一個星期裡,相距不過幾天。
島上胡巴爾信眾夠多,沒死的人可以幫忙清理這團混亂,但他知道對大夥兒來說,這是很痛苦的事情,對那些經歷過五年前事件的人更是如此,上次也一樣,神殿的莊嚴氣氛在瀰漫的火藥味中蕩然無存。也因此,陶斯長老看見進來的兩個人覺得寬心不少,那是兩個比較年輕的教士,一個是凱爾,另一個是彼多,他們穿過大洞走進來,那裡原本是兩扇壯觀的橡木拱門。
凱爾大概三十歲,彼多只有二十左右,但很多人第一眼會誤以為這兩人是雙胞胎,他們不只外表相仿,連氣質也接近。一方面他們穿著一模一樣,另一方面,將近十年來,凱爾可謂是彼多的精神導師,彼多下意識模仿凱爾銳利而謹慎的性格。兩個人都皮膚黝黑、留著平頭,套著一模一樣的棕色袍子,斷氣的那些教士也是。
兩個年輕教士要上祭壇察看陶斯長老的傷勢,但得先咬牙穿過一干弟兄的遺體才到得了。陶斯看著他們的困窘心裡難過,但只要看見他們就已安心一些,暖意湧上心頭,心跳也快了。前一小時裡,他一分鐘脈搏只有十下,對他來說心臟動得快一點、穩定下來是好事。
彼多還細心,拿了陶杯裝水給陶斯長老喝,前往祭壇的路上他注意著不讓水灑出來,但雙手還是不停顫抖,可見神殿裡的情景強烈衝擊他。他遞水給陶斯長老,不僅陶斯鬆口氣,彼多自己也是。長老兩手捧著壺,用剩下的力氣湊到嘴邊,沁涼泉水滑進喉嚨使他彷彿重獲新生,對於身體的痊癒也大有幫助。
「謝謝你,彼多。你不用擔心,不用到明天,我這把老骨頭就能回復。」陶斯一邊說一邊將杯子擱在地上。
「我相信長老會好起來的。」彼多說話也在抖,不像是很有信心,但至少還懷著一絲希望。
這是陶斯今天第一次露出笑容。彼多好純真、好體貼,他就身在這座喋血神殿裡面,也能夠令人相信事情都會好轉。十歲的時候,彼多雙親慘死在毒販手裡,他就被送到這座島上,與教士一同生活以後,他找到內心的平靜與勇氣,終於放下喪親之痛好好生活。看見彼多長大成人,而且這樣善良、仁慈、無私,陶斯一直為自己、為所有弟兄感到驕傲。天不從人願,現在他可得將這孩子送回當年剝奪他天倫之樂的世界去。
「凱爾、彼多,你們應該都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過來吧。」
「是,長老。」凱爾代表兩人回答。
「那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長老。如果長老覺得我們沒準備好,也不會叫我們過來了吧。」
「沒錯,凱爾。你果然思路清晰,我常忘記這點。彼多你別錯過,多跟凱爾學學。」
「我會的,長老。」彼多謙卑地回答。
「接下來我說的事情你們要聽好。時間不多了……」陶斯繼續說:「此刻起,每秒鐘都彌足珍貴,自由世界的延續或存在與否,已經成為你們肩膀上的重擔。」
「我們不會令長老,失望。」凱爾很肯定地回答最後兩個字。 「只是針對我的話,失望也無所謂。但是凱爾,這件工作沒辦妥,是全人類要失望……」陶斯頓了一下又重新開口:「找出石頭的下落,帶回這座神殿。黑暗降臨之時,石頭絕不可以落入惡人之手。」
「這是什麼意思?」彼多問:「長老,之後會怎麼樣?」
陶斯伸手搭在彼多肩上,以他現在的體能而言,是很大的力道。陶斯受到腥風血雨所震撼,也害怕即將到來的威脅,更重要的是他深感無力,除了派這兩個年輕人出去,居然沒有其他辦法了。
「你們兩個聽好,石頭落入有心人手中,時機一到,我們也躲不過了。到時候巨浪滔天,人類會像大雨中的淚水一樣全被沖走。」
「大雨中的淚水?」彼多重複了一次這段話。
「沒錯,彼多。」陶斯長老輕聲回答:「大雨中的淚水……你們得趕快出發,沒時間多解釋了,要立刻開始行動,每分每秒我們都更靠近世界末日,我們所知所愛的世界有危險。」
凱爾伸手輕碰長老的臉,替他抹去一道血漬。
「長老請別擔心,我們不會遲疑。」話雖如此,他還是猶豫了一陣,然後開口問:「但我們要從哪裡開始找?」
「孩子,一樣的地方。去聖塔蒙地迦,那裡有人想得到『月之眼』,一定是帶到那兒去。」
「但是……『有人』是說誰呢?是誰下的毒手?我們要找的是誰、還是什麼東西?」
陶斯長老停頓一會兒沒回答,看了看身邊慘況,想到自己曾經與凶手四目相交,接著對方朝他開了槍。
「凱爾,去找一個人,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你們在聖塔蒙地迦一帶打聽打聽,問問是不是有個殺不死的人,或者找到一個能單槍匹馬、完全不受傷就殺死三、四十個對手的人。」
「長老,如果真有這樣一個人,鎮上居民敢跟我們透露太多嗎?」
陶斯對這年輕人一連串的問題不耐,然而凱爾說的沒錯,他思考著。凱爾有個優點:他如果提出疑問,至少都是真的想過。這一次,陶斯還有辦法回答。
「你講的有道理,可是聖塔蒙地迦不一樣,那是個靠口袋裡東西辦事的地方……」
「口袋裡的東西?」
「錢哪,凱爾。外面世界的人,為了錢什麼事情都肯幹。」
「但是我們沒有錢吧?根據胡巴爾的律法,我們不使用金錢……」
「技術上來說是如此,」陶斯說:「不過其實我們有錢,不用而已。去碼頭找山謬弟兄,他會給你們一口箱子,裡面滿滿的都是錢,遠超過一個人一輩子所需。你們用這筆資金,在那邊收集情報吧。」說到這邊,陶斯覺得疲憊,還感受到巨大的悲慟,伸手摀住臉才能繼續往下說:「沒有錢的話,你們在聖塔蒙地迦撐不過一天吧,記住……不管你們想怎麼做,錢絕對不可以離身,行事謹慎、財別露白,不然引人覬覦,外頭壞人很多。」
「瞭解了,長老。」
凱爾心裡頭覺得刺激,他小時候就來到島上,這是第一次可以到外界走走。胡巴爾教士都是嬰兒時期到這座島,有些人是孤兒、有些人是父母棄養,成為教士後,一輩子都不一定有機會出去。只不過身為胡巴爾教士,凱爾對於自己居然期待旅行而生出強烈罪惡感,此時此景不能這樣想。
「長老還有要交代的事情嗎?」他問。
陶斯搖搖頭。「沒有了,孩子,出發吧。你們有三天時間可以奪回月之眼,以阻止世界滅亡,已經開始倒數計時了。」
凱爾與彼多對長老鞠躬行禮,轉身,戒慎恐懼地步出神殿。他們其實急著去外頭換換氣,神殿裡面滿溢的死亡氣息令人作嘔。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一旦離開這座島,只會愈來愈熟悉這個的味道。陶斯長老明白這一點,看著兩個年輕人離去,他真希望自己有勇氣可以說出外面世界的真實樣貌。五年前,他派了兩個年輕教士到聖塔蒙地迦,然而那兩人沒有回來,知道原因的只有陶斯一人。
注意事項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