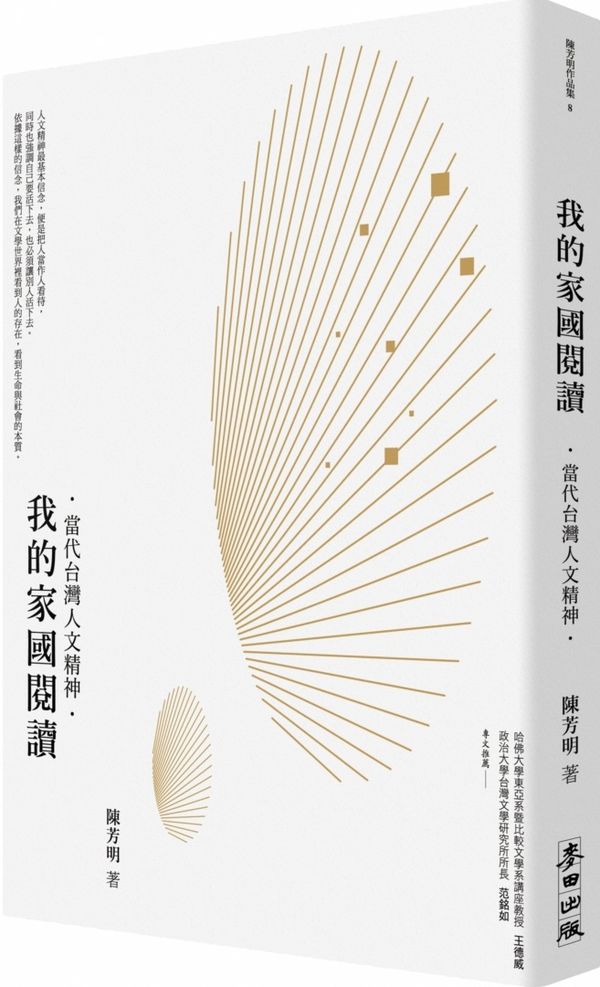本書適用活動
分類排行
-
我是誰?我在哪?「我」根本不存在──東方哲學奇才聯盟,帶你看穿人生bug
-
1分鐘圖解孫子兵法:拿破崙、曹操、李世民、麥克阿瑟、武田信玄、稻盛和夫都推崇,翻譯逾30國語言,千年兵法智慧,輕鬆掌握領導與應變之道!
-
1分鐘圖解三十六計:孫武、諸葛亮、曹操都在用,拿破崙、比爾蓋茲都在讀,看透人性,輕鬆掌握商場、職場與生活智慧,人人都能靈活運用的生存計謀!
-
室內空間計畫學【全新增訂版】:入門╱進階 最重要概念建立必備寶典,室內設計立體動線邏輯與實作力完全激發
-
如何蓋一座大教堂?:學習工程師「解決問題的思維」!從重大歷史工程到日常小物,一窺創新與發明背後的故事
-
律師帶你看校園大小事: 老師和家長必知的44個霸凌防制和性平觀念指南
-
圖解易經:讀懂《易經》的第一本書,全譯插圖暢銷版
-
罪、罪犯與他們的產地:第一本最接近台灣民情與文化的犯罪心理全解析,原來「罪」與「犯罪」和我們想的不一樣
-
茶杯與顱器:禪密相逢時
-
彩虹丹青:融合見地與修持的成就口訣
內容簡介
從中國到台灣、從戒嚴到解嚴、從殖民到媚外
各種文化、雙元史觀的融合與轉型
走出象牙塔的知識分子,從文學閱讀中探索、
觀察文學如何再現台灣社會,進一步檢驗當代人文精神
民主運動的展開,政治改革的翻轉,國際形勢的挑戰,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使整個社會再也不可能停留在戒嚴時期的寧靜與安定。學校的圍牆,再也抵擋不住變革力量席捲而來。知識分子留守在書窗裡的安頓,也不復存在。在知識實踐的時代,所有的思考者與書寫者似乎受到要求,如何把靜態思維化成具體行動。這恰恰就是當代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挑戰,也是檢驗人文精神的最佳時期。
而在閱讀中,我們發現文學容許我們看見女性受到歧視,原住民受到汙名化,農民工人受到剝削,同志受到扭曲。在靜態的文字之間遊走,終於激發讀者的批判行動。而這樣的批判,正好與我們所高舉的人文精神相互吻合。從文學閱讀中探索當代台灣人文精神,正是本書書寫的主要企圖。
本書重新探討文學對當代社會所帶來的衝擊。鼓勵讀者透過文學閱讀,進一步探索戰後台灣社會、政治、文化的演變。觀察文學如何再現台灣社會,如何從封閉的黨國體制走向開放的民主改革,如何使邊緣族群、性別、階級獲得發言權,從而進一步干涉政治權力。
【專文推薦】
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 王德威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 范銘如
目錄
推薦序
板塊與潮汐 王德威
隱形的力量 范銘如
緒論 什麼是人文精神?
第1章 面對台灣歷史傷口:一個歷史與文學的角度
第2章 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對決
第3章 殖民地與崇洋媚外的根源——帝國中心論的觀察
第4章 民主運動解放了什麼:七○年代的反思
第5章 誰先解嚴:文學或政治?
第6章 女性文學的意義:從人權立場出發
第7章 原住民文化的窺探:內部殖民的拆解
第8章 同志文學與台灣民主
第9章 和解為什麼可能
第10章 雙元史觀的建構及其實踐
第11章 本土.在地化.民族主義
後記 當前人文學的危機
內文試閱
走出象牙塔
文學作品只是屬於靜態的文字嗎?它只是限於藝術審美的領域嗎?或者,它竟只是創作者之間的文字遊戲嗎?這個議題已經存在許多人的觀念或偏見裡,好像已經鑄成定論,那樣牢固地進駐在學術界裡。文學研究者曾經受到強烈質疑,而且也不時被指控:「文學不能治療感冒,也不能治療香港腳。」是這樣嗎?好像理工科技才是真正的知識,是非常實用的學問。然而理工領域,如天文學、物理學,也不能治療感冒與香港腳。學術界對文學領域的偏見,並非真正理解文學的核心價值。長期以來,我希望換一個角度,重新探討文學在當代社會所帶來的衝擊。在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開授了兩個學期的課程,名稱是「文學與當代台灣人文精神」。這個課程設計,在於鼓勵學生透過文學閱讀,進一步探索戰後台灣社會、政治、文化的演變。現在時機已經成熟,可以具體寫出一冊專書,仔細觀察文學如何再現台灣社會,如何從封閉的黨國體制走向開放的民主改革,如何使邊緣族群、性別、階級獲得發言權,從而進一步干涉政治權力。
台灣社會曾經把學術研究視為象牙塔,這是許多人的看法,很少有人對這樣的概括反駁或抗拒。象牙塔(ivory tower)是一個西方舶來的名稱,在一定程度上,對知識分子抱持高度的貶抑。學者把自己關在象牙塔,也並非是罪大惡極。如果一個社會陷入混亂的意識形態鬥爭,或捲入惡劣的政治權力爭奪,學者反而可以獲得一個清楚思考的位置。所謂知識分子,是從英文的「intellectuals」翻譯過來的,意味著從事思考的人,可以實踐知識於他所賴以生存的社會或家國。這個名詞,跟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截然不同。士大夫在西方被譯為「literati」,指的是經過科舉考試的士大夫官僚(scholar-bureaucrats)。士大夫可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卻可以掌握權力,統治天下。這種畸形現象,曾經在中國延續數千年之久,使得民間與官方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德川儒學傳統開始有了變革。他們把「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論述,區隔成為兩種不同的範疇。從誠心到齊家,是屬於私領域,治國、平天下則是屬於公領域。在私領域的個人修養,是屬於個人道德的養成;而在公領域的治國、平天下,則是屬於實學。諸子百家的大傳統,無非都是在於成就個人的品格與道德。進入現代世界以後,凡是有關國家社會的重大決策,就必須透過新興的近代知識,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甚至是物理、化學、生物學、醫學,來實踐於現實的政策裡。這種儒家傳統的變革,是日本明治維新能夠成功的原因,他們全面向西方的近代知識開放,接受現代化思考的洗禮,終於完成脫亞入歐的現代化取向。
明治時期近代知識分子的格局,可以說與晚清的官僚士大夫劃清了界線。前者重視政策的具體實踐,後者仍然停留在道德修養的層面上。知識分子一詞,在中國的出現,恐怕必須要等到五四運動之後,才普遍使用。士大夫自我囚禁於象牙塔之內,在晚清時期並非是離奇現象。明朝的王陽明曾經提出「滿街都是聖人」,在當時可能是一種尊稱。但明朝滅亡的原因,便是滿街聖人仍然在空談心性。當知識與社會之間出現落差時,士大夫在關鍵時刻可能無法救國,反而是朝代顛覆的致命原因。
象牙塔的存在,並不是罪惡。如果知識分子擁有龐大知識,應該對當代社會也具有一定的發言權。在充滿挑戰的關鍵時期,無論是屬於科學領域或人文學科,知識分子往往被期待走出象牙塔。畢竟他們比起社會的各個階層,具備了更完整的知識論與世界觀。他們絕對有足夠能力,足以探知公共價值所受到的扭曲與貶抑。也許要他們承擔公平與正義的責任,似乎是一種苛求,但是指出真理或真相的偏頗與曲解,應該是所有知識分子的基本要求。在太平盛世,學術研究者當然是要關在室內進行專業的思考。當外面的社會現實發生價值混亂時,辨識政治權力的氾濫,或釐清意識形態的誤用,唯知識分子能夠勝任,並提出一個指引。學院或校園的圍牆,也許是構成象牙塔的藩籬。學者或知識分子,可以在圍牆之內進行冷靜的思考,從事深刻的知識追求,比起同時代的其他社會階層,知識分子確實可以獲得相當豐富的資訊。他們具備能力可以發現社會或政治的問題,也可以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知識並非是靜態的存在,無論是屬於方法論或實踐論,能夠活用它,就能夠翻轉政治權力的長期優勢。在殖民地時期,在戒嚴令時期,政治從來都是在干涉知識分子,阻礙他們的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這種單方面支配的優勢,經過一九七○年代民主運動之後,知識分子已經可以主動干涉政治。在到達可以干涉政治權力之前,台灣社會已經有多少左翼知識分子遭到逮捕並槍決,有多少右翼的自由主義者遭到查禁並審判。這種血跡斑斑的記憶,長期構成了台灣知識分子的噤聲與畏怯。在白色恐怖年代,無數的社會主義信仰者被冠以匪諜與通敵之名,而受到殘酷的人權迫害。台灣會變成極端右傾的社會,完全肇始於戰後初期的高度鎮壓。相形之下,可以合法地從事公開言論批判的追求,大多是屬於自由主義分子。從一九五○年代的《自由中國》,一九六○年代的《文星》雜誌,一九七○年代的《大學雜誌》,鮮明地鋪陳出台灣知識分子的思想軌跡。
在那蒼白而荒涼的年代,所有的雜誌都承受過被查禁的命運。雷震、殷海光、李敖、柏楊、彭明敏,都曾經羅列在台灣自由主義傳統的系譜裡。他們如果不是被監禁,便是被剝奪教職,或者是被迫遠走他鄉。歷史所給予他們的殘酷命運,終於沒有使他們保持沉默,只要有發言的空間,他們都各自提出內心所懷抱的理想社會。沒有這些前行者的努力,也許就無法預告日後台灣民主運動的誕生。他們擁有的利器,只不過是思想與文字。他們未嘗有一日使其理想獲得實踐,但是他們的著作卻為後來的知識分子提供無窮無盡的想像。
相對於早期靜態的知識分子,台灣在一九七○年代開始見證運動型知識分子的誕生。所謂運動型知識分子,指的是他們不再只是依賴靜態文字的發表,而是進一步與同時期的思想光譜接近者相互結盟。他們完全是時代的產物,如果沒有經歷過一九七○年釣魚台運動,如果沒有受到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的衝擊,如果沒有受到一九七二年華府與北京簽訂《上海公報》的影響,知識分子不可能走出書齋,而紛紛投入正在萌芽的草根民主運動。一九六○年,雷震雖然有過組黨運動的嘗試,卻在威權體制的破壞下,使構想中的中國民主黨胎死腹中。
在一連串國際事件的打擊下,國民黨在台灣所虛構的「中國體制」,逐漸顯露其欺罔性。聚集在《大學雜誌》下的本土知識分子,已經強烈感受台灣的歷史危機。他們一方面放棄國民黨黨籍,一方面主動參與選舉運動。其中的代表人物,當以許信良與張俊宏為具體例證。在那危疑時期,他們不僅具有論述能力,也具備了走出象牙塔的勇氣。他們比起雷震、殷海光還更具優勢的原因,就在於國民黨所高舉「代表中國」的旗幟,已被揭破是荒謬與謊言。這是一個結束的開始,黨外運動一詞逐漸形成全新的政治觀念,一方面暗示政治的中國性已注定要式微,一方面則彰顯文化的台灣性即將嶄露頭角。
走出象牙塔,是當代台灣知識分子的宿命。民主運動的展開,政治改革的翻轉,國際形勢的挑戰,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使整個社會再也不可能停留在戒嚴時期的寧靜與安定。學校的圍牆,再也抵擋不住變革力量的席捲而來。知識分子留守在書窗裡的安頓,也不復存在。在知識實踐的時代,所有的思考者與書寫者似乎受到要求,如何把靜態思維化成具體行動。這恰恰是當代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挑戰,也是檢驗人文精神的最佳時期。
什麼是人文精神?
傳統書生參與科舉考試時,或者獲得官位時,往往被要求必須寫出所謂的「策論」。這些策論是針對當時的政治形勢或經濟狀況,向皇室提出政策上的建議。以北宋為例,整個王朝不只受到北方契丹人的挑釁,也受到西夏人的「寇邊」,迫使天朝必須進行防禦戰爭。由於北宋強調中央集權,提倡文人政治,所以這些書生所提出的政策建言,往往都淪為空談。在他們的文字裡,充滿了非常腐朽的春秋觀念,再三強調尊王攘夷的崇高理想,因此當時所盛行的弭兵論,都只能證明書生空議論而已。在舊社會裡,知識與現實總是出現巨大落差,他們可以提出陳義甚高的言論,卻無法在殘酷的現實世界具體使用。
士大夫的思維,能夠支配傳統社會長達千年之久,完全是受到科舉制度的庇蔭。他們提出的建議,或傳播的言論,大多數是屬於反智論(anti-intellectualism)。表面上是非常雄辯,骨子裡卻是極其空洞。這種現象,必須要到一九○五年慈禧太后廢除科舉考試之後,知識領域才逐漸有了改觀。緊接著五四運動崛起之後,當時知識分子如胡適、魯迅,開始展開對儒家思想或傳統文化的嚴厲批判。那種蔚為風氣的反傳統論(anti-traditionalism),正是現代知識分子的一次徹底反省。台灣社會的知識現代化,並沒有與五四傳統緊密連接起來。他們在殖民地裡所接受的現代教育,就已經脫離傳統儒家思想的桎梏。殖民地孩童在公學校所受的教育,包括國語、歷史、數學、博物,已經與中國傳統的四書五經截然不同。
台灣第一代知識分子誕生的時間,大約在一九一五年左右,也就是噍吧哖事件受到殘酷鎮壓的那年。知識分子一詞,無論是思考或行動,已經與中國士大夫的條件有了全然不同的取向。他們所受的知識訓練,在走出學校之後,便是要把所有學習的成果具體實踐於社會。一九二○年,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所組成的新民會,創辦了《台灣青年》的刊物,開始介紹當時全世界最新的思潮,並且也針對殖民地所面臨的畸形統治,提出他們的見解。無論是他們所吸收的理論,或是對殖民地社會的分析,他們的言論高度完全可以與現代思潮相互比並。發軔於一九二○年代的啟蒙運動,對於後來政治團體的衝擊,不可不謂巨大。這些政治團體包括:台灣文化協會(1921)、台灣農民組合(1926)、台灣民眾黨(1927)、台灣共產黨(1928)、台灣地方自治聯盟(1929),在思想光譜上,從極右到極左的政治立場,都同時浮現。
日據時期以降的台灣知識分子,便是要糾正殖民統治所帶來的人格扭曲。當他們提到台灣人時,「人」的價值觀念都受到尊崇。這樣的「人」,涵蓋了人本、人權、人文的廣泛定義。這些都牽涉到文化內容的問題,確切而言,凡是有關種族(race)、階級(class)、性別(gender)的議題,都是當時台灣知識分子的關心所在。在面對日本的種族優越論時,知識分子提出了台灣人本位論。在面對日本資本家壟斷所有的利益時,他們站在農民與工人的立場提出批判。在面對統治者男性中心論的支配時,他們也會站出來為台灣女性講話。
他們的思考與行動,可以說非常符合當代所說的人文精神(humanism)。知識分子在殖民地時期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多元,從最基礎的啟蒙工作,到思想傳播,終而創辦雜誌與報紙,足以顯示他們對自己所具備的身分相當警覺。稍後他們所介入一九二○年代的政治運動,以及一九三○年代的文學運動,無非都是台灣人文精神的延伸。無論是左派或右派知識分子,他們在訴諸具體行動時,都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他們受到逮捕審判,或是思想遭到檢查,根本無所遁逃,而必須為自己發表的語言或文字負起責任。他們在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果敢行動,無疑是為後代的知識青年塑造典範。
什麼是人文精神?這個語詞的誕生,其實是因應現代科技的到來。「人」的發現,是文藝復興以降的重要議題。當他們的知識逐漸脫離教會的控制,人的意義不再是神學的附庸,而是一個可以思考、可以批判、也可以行動的肉身,也是可以藉由理性的判斷,建立一個全新的文化秩序。啟蒙運動之後,西方知識分子開始在科學方面開啟無限的想像,近代知識所包括的化學、數學、物理學次第建立起來,而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也持續開拓出來。一個以人為中心的知識領域慢慢構築完成。十九世紀中期發生的工業革命,使人類更進一步創造科技文明,那種大量生產、大量複製的時代,也接踵而來。
機械文明開始統治整個世界,人的意義也因而逐漸萎縮。在整個龐大的工業社會裡,作為人的單位愈來愈渺小,有人稱之為「原子化」(atomization)。人類藉由近代知識建立起來的工業文明,證明了科學並不必然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利用科學文明來製造戰爭,使人類陷入兩次大戰的災難,已經證明人類的智慧是極其有限。所謂現代性(modernity),一言以蔽之,便是指人的理性(reason)。當人的理性高過所有的世俗價值,它的地位無疑已經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利用理性的判別,利用科學的優越性,來建立種族歧視、階級歧視、性別歧視,正是二次大戰以降人類所面臨最急迫的危機。
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重新提出人文精神的議題,是不是已經過時了?是不是會被嫌棄是一個老掉牙的問題?身為一個文學研究者,或許只要把文學內容的研究做好,便已經相當盡職了。然而,在文學閱讀中,慢慢會發現所有的作品並非只是靜態文字的演出。作家在他的書寫中所呈現的世界,往往是讀者未曾思考或從未到達的境界。在閱讀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了台灣社會一直都存在著族群歧視、階級歧視、性別歧視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可能不像西方社會那樣,是由工業文明造成。島上發生的文化衝突,其根源往往來自歷史的殘餘,政治的多餘,而這正是本書所要面對、處理並解決的。
戰後初期的族群歧視,來自中華民族主義的高漲,以及台灣人所接受的日本文化遺產。兩種不同的歷史經驗相遇時,都各自產生兩極的想像、與相反的看法。在戒嚴時期,省籍問題也不斷衍生、氾濫,尤其是外省族群多劃歸在軍公教的社群裡,而本地族群則多是屬於一般工商業的庶民。一九七○年代本土運動崛起後,又開始出現統獨問題。政治主張使得知識分子也分別隸屬於不同意識形態的團體。一九九○年代,政黨政治開始萌芽時,整個社會又陷入藍綠對決。這已經不是政治議題所能概括,其中還牽涉到經濟、社會、文化的內容。
人文精神最基的本信念,便是把人當作人看待,同時也強調自己要活下去,也必須讓別人活下去。依據這樣的信念,我們在文學世界裡看到人的存在,看到生命與社會的本質。文學不再是靜態的書寫,它所呈現外在社會的偏見、歧視、貶抑,絕對不是向壁虛構。作家以敏銳之眼洞察人間的不幸與偏頗,把他們所看到的事實化為故事,呈現在讀者面前。作家的想像可能被視為虛構,但是他們確實到達社會最徹底最深層的邊境。從那裡他帶回來訊息,呈現給他的讀者。文學容許我們看見女性受到歧視,原住民受到污名化,農民工人受到剝削,同志受到扭曲。在靜態的文字之間遊走,終於激發讀者的批判行動。而這樣的批判,正好與我們所高舉的人文精神相互吻合。從文學閱讀中探索當代台灣人文精神,正是本書書寫的主要企圖。
延伸內容
◆編輯推薦——本篇收錄於第593期城邦讀饗報,立即閱讀更多內容!GO
◎文/麥田出版編輯 林賽琪
我曾有幸旁聽陳芳明老師在政大開設的「當代台灣人文精神」課程,課堂上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師說他週末要去抗議現場,那堂課結束時,老師和大家道:「我們現場見!」
就這麼一句簡單卻有力的:「我們現場見!」將上課時提到的歷史意識、文學運動、民主運動、女性意識、同志權利……全帶在身上,隨時隨地行動、出發。這樣一堂課,得到的不只是知識,更多的是陳芳明老師的身體力行,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為學生們親身示範、真實實踐。
《我的家國閱讀:當代台灣人文精神》,則是行動付諸文字的實踐,一筆一畫寫下老師對當代台灣人文精神的回顧與期待。從老師的慣常閱讀中,抽絲剝繭理出在歷史洪流中的此消彼長、充滿台灣性格的人文精神。讀畢全書,除了能充分理解從過去到現在的我們所身處環境中的人文環境,也能展望未來,看看自己如何成為台灣人文精神的一分子。
立即訂閱城邦讀饗報!GO作者資料
陳芳明
一九四七年出生於高雄。曾任教於靜宜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後赴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任教,同時成立該校台灣文學研究所,目前為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著作等身,主編有《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選文篇》、《余光中跨世紀散文》等;政論集《和平演變在台灣》等七冊;散文集《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巷》、《掌中地圖》、《昨夜雪深幾許》、《晚天未晚》;詩評集《詩和現實》、《美與殉美》;文學評論集《鞭傷之島》、《典範的追求》、《危樓夜讀》、《深山夜讀》、《孤夜獨書》、《楓香夜讀》,以及學術研究《探索台灣史觀》、《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灣新文學史》,傳記《謝雪紅評傳》等書,為台灣文學批評學者的研究典範。
注意事項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