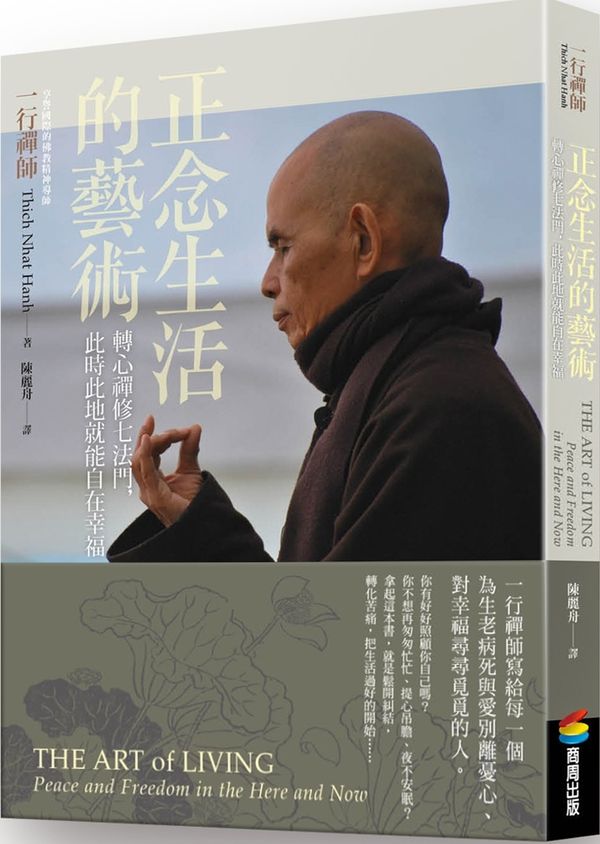第一章 空:相即的奇蹟
空意味著充滿了萬事萬物,
卻沒有個別獨立的存在。
想像一朵美麗的花兒,片刻即可。那朵花可能是蘭花或玫瑰,甚至是長在路邊一朵不起眼的小雛菊。看著一朵花,我們可以看到它充滿著生命。花兒含納著土壤、雨水和陽光,花朵裡也充滿了雲、海洋和礦物,甚至充滿空間和時間。事實上,整個宇宙就存在於這一朵小花。如果我們拿掉這些「非花」的成分,花朵就不存在。沒有土壤的養分,花朵不會成長。沒有雨水和陽光,花朵會枯萎。除去非花的成分,不會留下任何我們可以稱之為「花」的實體。這樣的觀察告訴我們:花朵裡充滿整個宇宙,沒有分別的存在。花朵無法單憑自身而存在。
我們也都充滿太多事物,沒有單獨的自我。如同花朵,我們包含泥土、水、空氣、陽光和溫暖。我們包含著空間和意識。我們包含了我們的祖先、我們的雙親和祖父母、教育、食物與文化。我們是整個宇宙相聚在一起所創造出的奇妙示現。如果除去了這些「非我」成分的任一個,將沒有所謂的「我」。
空:第一解脫門
空,並不表示無。說我們是空的,並不意味我們不存在。無論一個東西是滿的或空的,首先它必須先在那裡。當我們說一個杯子是空的,為了是空的,那個杯子必須在那裡。當我們說我們是空的,意味著為了沒有永恆、單獨的自我,我們必須在那裡。
大約三十年前,我在尋找用來形容我們和其他所有事物深刻相互關聯的英文用語。我喜歡「密不可分」(togetherness)這個詞,但最後採用「相即」(interbeing)。動詞to be(存在)可能造成誤導,因為我們不可能單憑我們自身而存在。「存在」(to be)總是「相互存在」(inter-be)」。如果我們將前置詞 inter 和動詞 to be 組合在一起,就有了一個新的動詞 inter-be。To inter-be(相互存在)更正確地反映了實相。我們彼此相即,我們和所有生命相互依存。
我非常欣賞一位名為路易士.湯瑪斯(Lewis Thomas)的生物學家的作品。他描述我們人類的身體如何被其他無數的小小有機體「分享、租用和占據」,沒有這些小小有機體,我們不可能「動動肌肉、敲敲手指或想想點子」。我們的身體是一個社區,體內數以兆計的非人類細胞甚至比人類的細胞更多。沒有它們,我們此刻不可能存在這裡。沒有它們,我們無法思考、感覺或說話。路易士說,沒有單獨的存有。整個星球是一個巨大、生氣勃勃、會呼吸的細胞,所有運作的局部皆共生地鏈結在一起。
相即的智慧
日常生活中就可以觀察到空性和相即。看著一個小孩,我們很容易在她身上看到她父母親和祖父母。她看待事物的方式、她舉手投足的模樣、她談論的事,甚至她的技藝和天分,都和她雙親一樣。有時候如果我們無法了解一個孩子為何表現出某種樣子,要記得她不是單獨存在的自我實體(self-entity)。她是一個延續的存在。她的雙親和祖先在她之內。當她走路和說話時,他們也一樣在行走和說話。看著孩子,我們就能觸及她的雙親和祖先;同樣地,當我們看著父母,也能看到小孩。我們並非獨立的存在,我們皆相即。萬事萬物為了示現,都必須依賴宇宙中其他一切事物,不論是星辰、雲朵、花兒、樹木,或你和我。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倫敦沿著街道行禪時,看到書店櫥窗裡擺著一本書,書名是《我的母親,我自己》(My Mother, Myself)。我並沒有購買那本書,因為我感覺自己已經知道書的內容。我們每個人確實都是我們母親的延續;我們就是我們的母親。因此無論何時我們對父母生氣,我們也是在對自己生氣。無論我們做什麼,我們的父母都與我們一起做。這或許令人難以接受,但千真萬確。我們無法說我們不想和父母有任何關係。他們就在我們之中,我們就在他們之中。我們是我們所有先祖的延續。而因為無常,我們有機會將我們所繼承的朝美麗的方向轉化。
每次我在禪修中心的佛龕前獻香或頂禮時,我並非以個別的自我,而是身為整體的傳承者來做這件事。每當我走路、就坐、進食或練習書法時,我都覺知到我所有的祖先此時此刻都在我之中。我是他們的延續。無論我正在做什麼,正念的能量使我能夠身為「我們」而做,而非只是「我」。當我手握毛筆時,我知道我無法將父親從我的手去除。我知道我不能將母親和先祖們從我身上去除。他們總是存在於我所有的細胞中、我的儀態舉止間,以及我能夠畫一個漂亮的圓的能力上。我也無法將我的心靈導師從我手中抹去。他們就存在我享受平靜地、專注地、正念地握筆畫圓的片刻間。我們所有人皆一起畫著圓圈,沒有單獨的自我在做這件事。在我練習書法時,我領悟到無我那深奧的智慧。它變成一種深刻的禪修。
不論在職場或家裡,我們都可以練習在一舉一動間看見我們的祖先與導師們。當我們表現出一項他們傳承下來的才能或技藝時,我們可以看見他們的臨在。當我們準備餐飯或清洗碗盤時,我們能在我們身上看到他們的雙手。我們可以體驗這種深刻的連結,避免落入我們是單獨自我的想法。
我們是一條河流
我們可以從遍及各處的相即來深觀空性——我們與周遭每樣事物和每個人的關係。我們可以從遍及各處的無常來深觀空性。無常意味著在兩個相續的時刻,沒有任何事物可以維持不變。希臘哲學家愛菲斯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of Ephesus)說:「你不可能兩次都涉入同一條河流中。」河水總是在流動,因此只要我們一爬上河岸,再次涉入河中水就已經變了。甚至在短短的時空中,我們也已經改變。我們的身體細胞每秒都在死去和生成。我們的思維、感知、覺受和心態也是時刻都在變化。因此我們不可能二次在同一條河流中游泳;河流也不可能二次迎接到同樣一個人。我們的身體和心思是不斷變化的連續體。雖然我們和前一刻看起來似乎是相同的,也依舊稱呼同樣的名字,但我們是不同的。不論科學儀器多麼高端複雜,我們無法在個人之中找到維持同樣不變而我們稱之為靈魂或自我的東西。一旦我們接受無常的實相,我們也必須承認無我的事實。
觀空性和觀無常可以幫助我們不落於認為我們是單獨且分別的自我。這種智慧可以幫助我們從錯誤知見的牢籠裡跨出來。當我們看著一個人、一隻鳥、一棵樹或一塊石頭,我們必須訓練自己保持空性的智慧。這和打坐冥思空性非常不同。我們必須真實地在我們自身和他人身上諦觀空性、相即和無常的本性。
例如,你稱我為越南人,你可能相當確定我是越南僧人。但事實上從法律層面來說,我沒有越南護照。從文化層面來說,我身上有法國的成分,也帶有中國文化,甚至印度文化。在我書寫和教學時,你可以發現數個文化淵源。從民族層面來說,並沒有所謂「越南族」。我身上有美拉尼西亞人(Melanisian)的成分、印度尼西亞人的成分,以及蒙古人種的成分。就像花朵是由非花的成分所構成,我也是由非我的成分所組成。這種相即的智慧有助我們接受無分別的智慧,讓我們自由。我們不會再想僅僅歸屬於某一地理區域或文化認同,而是在我們身上看到整個宇宙的展現。愈是以空性的智慧來諦觀,我們就能發現愈多,理解也愈深刻。這自然而然會帶來慈悲、自在和無懼。
請以我的真名喚我
我記得一九七○年代的某一天,當我們還在為巴黎的越南佛教和平代表團(Vietnamese Buddhist Peace Delegation)工作時,有可怕的消息傳來。許多人搭船逃離越南,這向來都是非常危險的旅程,不僅有暴風雨的威脅,也缺乏足夠的燃料、食物或水,而且還有遭遇活躍於泰國沿海的海盜襲擊的風險。我們聽聞的故事是一場悲劇。海盜強行登船,拿走值錢的物品,強暴了一個十一歲大的女孩。女孩的父親試圖反抗,被海盜丟入海中。女孩被侵害之後也投水自盡。父女雙雙喪命於大海。
我聽到這個消息後無法入睡。我感到強烈的悲傷、同情和憐憫,但是身為一個修行人,我們不能讓憤怒和無助的情緒癱瘓我們。於是我透過行禪、靜坐和正念呼吸,更深入諦觀這個情況,試著理解這一切。
我觀想自己是一個出生於泰國貧困家庭的小男孩,父親是目不識丁的漁夫。一代傳一代,我的祖先們生活在窮苦中,未受教育,也未獲援助。我也沒有讀任何書,甚至在充滿暴力的環境下長大。某一天,有人找我出海當海盜賺大錢,我也傻傻地答應了,渴望著終能打破貧困的不幸輪迴。然後,在同儕的壓力下,又沒有海防巡邏的制止,我強暴了一位美麗的女孩。
從來沒有人教我如何去愛或如何理解。我從未接受過任何教育,也沒有人讓我看到未來。如果你也在那船上,帶著一支槍,你可能已經朝我開槍。你可能會殺死我,但是你絕不可能幫得了我。
在巴黎那個夜晚的禪觀,我看到數百名嬰孩在相似的環境下誕生,而且他們將長大成為海盜,除非我現在做些什麼去幫助他們。我看到這一切,然後我的憤怒退去。我的內心充滿了同情和寬恕的能量,我不僅能將那個十一歲大的女孩擁入懷中,也能擁抱那個海盜。我可以在他們身上看到我自己。這是深觀空性、深觀相即所結的果實。我可以看到苦難不僅是個人的,也是集體的。苦難透過我們的祖先傳給我們,或者苦難就在我們身旁的社群。當我的責難和瞋恨被驅散,我下定決心終我一生皆要幫助受害者,也要幫助加害者。
因此,如果你稱呼我為釋一行,我會說:「是的,就是我。」如果你把我稱作那個年輕女孩,我會說:「是的,就是我。」這些都是我的真名。如果你把我稱作戰區那些沒有未來的赤貧孩童,我會說:「是的,就是我。」如果你把我稱作販售武器擁護戰爭的軍火販子,我會說:「是的,就是我。」所有這些人皆是我們,我們和每個人皆相即。
當我們能夠擺脫人我分別的想法,
我們會擁有慈悲,我們會擁有理解,
以及擁有幫助他人所需要的能量。
真理的兩種層次
在日常語言中,我們會說「你」、「我」、「我們」、「他們」,因為這些指稱是有用的。它們可以識別我們所談論的對象,但了解它們僅是傳統的指涉也是重要的。這些用詞只是相對真理(世俗諦),而非究竟真理(勝義諦)。我們遠遠超過這些標籤和範疇。在你和我和在宇宙之間強畫一條分隔線是不可能的。相即的智慧有助我們與空性的勝義諦連結。空性的教義並不是關於自我的「死去」。自我不需要去死。自我僅是一個想法、一個幻影、一個錯誤知見、一個概念;它並非真實存在。一個不存在的東西怎麼可能死去呢?我們不需要去殺死自我,但是我們可以透過對實相獲致更深的理解,來去除有個單獨的自我這樣的錯覺。
無所有者,無主人
當我們把自己看作一個單獨的自我、一個單獨的存在,我們認同我們的想法和身體。我們認為我們是身體的主人或所有者。我們可能會想「這是我的身體」或「這是我的心識」,就像我們會想「這是我的房子」、「這是我的車子」、「這些是我的資格證書」、「這些是我的感受」、「這些是我的情緒」、「這些是我的苦惱」。事實上,我們不該如此理所當然。
當我們思考或工作或呼吸時,許多人相信在我們的行動背後,一定有一個人格(person),一個行動者(actor)。我們相信一定有「某個人」在做那個行為。但是當風吹起時,風的背後並沒有一位吹風的人;只有風,如果風沒有在吹,就一點風也沒有。當我們說「正在下雨」(It is raining.),不需要一個下雨的人來下雨。誰是下雨的那個它(it)呢?只有下雨。雨正在下。
同樣地,在我的行動之外,沒有一個人,沒有我們稱為「自我」的東西。當我們思考時,我們就是我們正在運轉的思考。當我們工作時,我們就是那正在進行的工作。當我們呼吸時,我們就是那一進一出的呼吸。當我們行動時,我們就是我們的行動。
我記得看過一幅漫畫,描繪法國哲學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站在一匹馬前面,手指指向空中,說:「我思,故我是。」(I think, therefore I am.)在他後頭的那匹馬納悶著:「你是『什麼』?」
笛卡兒嘗試論證自我的存在。依據他的邏輯,假如我正在思考,那麼就一定有一個「我」為了進行思考而存在。假如我不存在的話,那麼誰在進行思考呢?
我們不能否認思考正在進行。顯然思考正在發生。大多時候問題就在於太多思考正在發生——想著昨天,擔憂著明天——所有這些思考都把我們從自身帶走,把我們從此時此地帶走。當我們陷入思索過去和未來,我們的心就沒有和我們的身體在一塊兒,與當下在我們之內與周遭的生命失去了連繫。因此,更為正確的說法或許是:
我思(過多),
故我是(沒有活在此時此地)。
要描述思考的過程,最精確的方式並不是說「某個人」正在思考,而是「思考正在顯現」(thinking is manifesting),是眾多條件聚合(因緣和合)而成的非凡、奇妙的結果。我們不需要為了思考而有一個自我存在;思考正在進行,只有思考。沒有一個額外的單獨存有者(entity)在進行思考。只要有思考者,則思考者就和思考同時存在。如同左邊和右邊的關係,你不可能僅有一邊,而沒有另一邊。他們在同一時刻顯現。只要有一個左邊,就會有一個右邊。只要有一個思考,就會有一個思考者。思考者就是思考。
身體和行動的關係也是如此。數百萬個神經元在我們的大腦裡一起合作,不斷地溝通。他們和諧地行動,產生一個動作、一種感受、一個念頭或一個知覺。那裡並沒有一個指揮,沒有做決定的頭兒。我們無法在腦袋或身體任何部位找出控制每件事的所在。有思考、感受、知覺的行動,但沒有行動者,也沒有進行思考、感受和知覺的單獨的自存者(self-entity)。
一九六六年,我在倫敦大英博物館裡注視著一具屍體,產生相當強烈的體驗。那具屍體被自然地保存在沙土中,以胎兒的姿勢躺著,已超過五千年。我佇立在那兒許久,非常專注地看著那具屍體。
幾個星期後在巴黎時,有天我在午夜突然醒來,很想要摸摸我的雙腿,檢查看看我有沒有像那樣變成一具屍體。時鐘指著兩點,我坐起身來。我深觀那具屍體和我自己的身體。大概坐了一個小時左右,我感覺像是水從山間傾瀉而下——沖刷啊,沖刷!最後我起身並寫下一首詩。我將這首詩稱作「大獅子吼」(The Great Lion’s Roar)。感受是那樣地明晰,意象肆意自如地流漫;靈思汩汩湧出,就如大水箱被打翻一樣。這首詩的開頭如下:
一朵白雲飄浮在天空
一束花兒盛開
漂浮的雲朵
盛開的花兒
雲在飄
花在開
我看得很真切,如果雲朵不在飄浮,它就不是雲朵;如果花兒不盛開,它就不是花。沒有開花,就沒有花朵。我們無法將二者分開。你不能將心識(mind)從身體拿出來,也無法將身體從心識中取出。兩者相即。我們在盛開間看到了花朵,我們在行動的能量中看到了人類。沒有行動的能量,就沒有人類的存在。如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tre)的名句:「人是他的行動之總和。」我們是我們所思所言與所作所為的總和。正如一棵橙樹生出美麗的花朵、葉子和果實,我們也生出思考、言說和行動。如同橙樹一般,我們的行動總是隨著時間日漸成熟。我們只可以在我們的身體行動、言說和心識中發現自己,持續不斷猶如穿越時空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