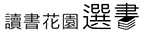- 庫存 = 7
 放入購物車
放入購物車 放入下次購買清單
放入下次購買清單
歷史的目擊者:以圖像作為歷史證據的運用與誤用
- 作者:彼得.柏克(Peter Burke)
- 出版社:馬可孛羅
- 出版日期:2022-03-01
- 定價:680元
- 優惠價:72折 490元
- 優惠截止日:2025年9月29日止
-
書虫VIP價:490元,贈紅利24點
活動贈點另計
可免費兌換好書 - 書虫VIP紅利價:465元
- (更多VIP好康)
本書適用活動
分類排行
-
律師帶你看校園大小事: 老師和家長必知的44個霸凌防制和性平觀念指南
-
裝潢工法全能百科王【暢銷典藏版】:選對材料、正確工序、監工細節全圖解,一次搞懂工程問題
-
黃金的傳奇史:拜金6000年,黃金如何統治我們的世界
-
30堂帶來幸福的思辨課:多想一點,發現更有深度的自己
-
一分鐘大歷史:從地理大發現、世紀瘟疫到車諾比核災,160個改變世界的關鍵事件完全圖解【二版】
-
英雄也有這一面:不要問,很可怕!華盛頓拔黑奴牙齒做假牙?愛迪生跟鬼講電話?33個讓你睡不好的歷史顫慄真相
-
被誤解的加薩:加薩是什麼地方?透視以巴衝突的根源
-
爆紅、成癮、愛馬仕:一位英國教授的社群媒體臥底觀察
-
不正義的地理學:二戰後東亞的記憶戰爭與歷史裂痕
-
阿德勒論兒童教育:個體心理學大師阿德勒帶你理解孩子的行為、情緒與內在需求
內容簡介
★新文化史權威彼得.柏克★
★二十年經典著作全新繁中譯本★
★售出超過10國版權★
專業期刊《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美國圖書館學會《選擇》(Choice)、《藝術與文獻》(Art Documentation),齊聲讚譽。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副教授兼所長——蔣竹山 深度導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陳建守 專業推薦
「假為真,真為假。這不是一場關於是否該使用圖像為歷史證據的辯論,更是關乎該如何使用。 」——新文化史權威 彼得.柏克(Peter Burke)
▏一畫勝千言? ▏
自二○○一年《歷史的目擊者》第一版發行以來,已過了將近二十年,該年,也是世貿大樓恐攻畫面,將恐懼無孔不入地帶入世界各地觀眾家中的一年。從此,對於圖像作為政治上、法庭上、歷史研究的證據,人們的興趣大為增加。近年社群平台散佈全球,人們對於「假新聞」散播的擔憂,開始不僅只針對文字,也延伸到圖片上。
新文化史權威彼得.柏克(Peter Burke),認為有必要在此時,重新審視與討論圖像的地位、能力,及其做為歷史證據的應用及影響。
往常,若歷史學者使用圖像,通常只把它們當作單純的插圖處理,卻未從圖片本身的背景深入分析。但圖像的多樣性與用途,以及不同歷史時期中對圖像的態度,需要放在「脈絡」下被檢視,包括藝術、宗教與政治背景、美學觀點、精神分析、符號學、觀眾反應等。若忽略這些脈絡,其風險性在於,以觀者對圖像的認知去分析特定的歷史意義及影響,結果可能並不正確,對於研究分析也有所損害。
作者跨地區、跨時期、跨傳播媒介研究多種圖像,從貝葉掛毯,到宗教圖像、政治圖像、廣告圖像、商品圖像……深入且全面鑽研圖像的實際用途。透過名家作品或文句,教導讀者如何從圖像中剖析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了解背後隱含真義,並避免錯誤解讀的陷阱。
▏彼得・柏克提出判讀圖像證據十誡。▏
1:一幅既有的圖像是出自於直接觀察,還是源自於另一幅圖像。
2:把圖像置放在文化傳統中,包括在某個既定時間地點中所流通的再現慣例或符號。
3:注意細節,越深入背景中就越可靠,因為藝術家並不是為了證明什麼而使用這些細節。
4:研究「後製」、「接受度」和「再利用」,用以揭示出圖像過去的功能。
5:要意識到操縱的可能性,包括數位操縱。
6:要意識到中介者(們)的存在。誰製作的?所處的位置是否足以好好觀察被再現的對象?
7:可能的話,比較關於相同物件或事件的不同圖像,兩個或以上的見證總比一個好。
8:留意圖像脈絡,或更正確地說,是複數形式的脈絡,包括物質的、社會的、以及政治的。
9:要意識到圖像的作用,以及它們對於外界影響。
10:最後一條,就是「沒有」規則,由於圖像本身的多樣性,還有歷史學者打算提問的問題,也充滿多樣性。
目錄
第一章:照片與肖像
第二章:圖像誌與圖像學
第三章:神聖與超自然
第四章:力量與抗議
第五章:圖像中的物質文化
第六章:社會景象
第七章:他者的刻板印象
第八章:視覺敘述
第九章:從見證者到歷史學者
第十章:超越圖像學?
第十一章:圖像的文化史
內文試閱
導論:圖像的見證
本書主要討論的是圖像作為歷史證據的使用。之所以寫作這本書,不僅是為了鼓勵這類證據的使用,同時也是為了提醒潛在使用者一些可能犯下的錯誤。大約在上個世代時,歷史學者們的興趣大幅擴展,範圍不僅包括政治事件、經濟潮流和社會結構,還包括了心態史、日常史、物質文化史、身體史等等。若他們自限於傳統資料,例如由行政當局製作並存檔的官方文件,那麼他們就不可能在這些相對新興的領域內進行研究。
基於這樣的理由,學者們越來越常使用更大範圍的證據,而在文獻和口述見證之外,圖像也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就以身體史為例。圖片指引出關於疾病與健康方面不斷改變的觀點,而在同樣不斷改變的審美標準方面,或是男女對個人外貌的關注歷史方面,圖片甚至可能更加重要。同樣地,若沒有圖像的見證,第五章將討論到的物質文化史實際上就不可能辦到。而正如第六與第七章試圖闡明的,圖像的見證對心態史也具有重要貢獻。
視覺的不可見性?
歷史學者很有可能還不夠認真對待圖像的證據,因此一九九八年的一場討論提到了「視覺的不可見性」。正如一名藝術史學者所言:「歷史學者……偏好處理文本和政治經濟方面的事實,而不是圖像所探究的更深層經驗」,而另一名學者則指出這其中所意味的「對圖像的高傲態度」。
若和那些根據書寫及繕打文獻進行研究的歷史學者相比,以照片檔案進行研究的歷史學者則相對少數。附有插圖的歷史期刊同樣相對少數,即使有,也是相對少數的作者會利用這個機會。若歷史學者真的使用了圖像,他們通常只把它們當作單純的插圖處理,把它們複製在書裡,不做任何評論。即使文本中討論到這些圖像,這項證據通常也是用來闡明作者藉由其他方式所達到的結論,而不是用來提出新的答案或發出新的問題。
為何該是這種狀況呢?已故的拉斐爾.塞繆爾(Raphael Samuel)在一篇文章裡描述他在維多利亞時期照片中的發現,他把自己和其他同時代的社會史學者們形容為「視覺文盲」。他是一九四O年代的孩子,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從前和現在都是「完全屬於電視普及以前」的孩子。他在學校和大學裡的教育,都是關於閱讀文本的訓練。
儘管如此,此時已有一小群重要的歷史學者們開始利用圖像的證據,尤其當他們的專長領域是在書寫文件極少或根本不存在的時期。例如,若沒有阿爾塔米拉(Altamira)或拉斯科(Lascaux)洞穴壁畫的證據,要撰寫關於歐洲史前歷史的確相當困難,而若沒有墓室繪畫的證明,古埃及的歷史也會變得難以估量地貧乏許多。在這兩個例子中,圖像實際上提供了社會活動的唯一證據,比如狩獵。有些研究較後期歷史的學者也認真對待圖像。例如,研究政治態度、「公眾意見」或政治宣傳的歷史學者,長期以來都在使用版畫證據。類似地,傑出的中世紀專家大衛.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在半個多世紀以前,便已主張貝葉掛毯(Bayeux Tapestry,圖78)是「英國史的第一手資料」,並且「值得和《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及普瓦提埃的威廉(William of Poitiers)的紀錄一併研究」。
這些由少數歷史學者進行的圖像運用可以回溯到更早以前。如同法蘭西斯.哈斯基爾(Francis Haskell,1928–2000)在《歷史與其圖像》(History and its Images)中所指出的,十七世紀時人們研究羅馬地下墓穴中的繪畫,作為早期基督教歷史的證據(以及在十九世紀時作為社會史的證據)。
在十八世紀初,貝葉掛毯已被學者們視為歷史資料而認真看待。在十八世紀中葉,一名評論家對克勞德-約瑟夫.韋爾內(Claude-Joseph Vernet,1714–1789)的一系列法國海港繪畫表示讚賞,他評論道,若有更多畫家追隨韋爾內的範例,那麼他們的作品會對後代更為有用,因為「在他們的繪畫中,將有可能讀到關於風俗、藝術與國家的歷史」。
文化史學者雅克伯.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與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本身也是業餘藝術家,他們分別在撰寫關於文藝復興與「中世紀之秋」時,除了當時的文本以外,也利用像拉斐爾及范艾克這樣的藝術家畫作,建立起他們對義大利及荷蘭文化的描述與詮釋。布克哈特在進入文藝復興大眾文化的討論之前,先描寫了義大利的藝術,他將圖像與紀念像形容為「過去階段的人類精神發展之見證」,透過這些物件,「有可能讀出某段時間關於思想與再現的架構」。
至於赫伊津哈,一九O五年他在格羅寧根大學(University of Groningen)發表了他的就職演說《歷史思想中的美學要素》,當中他將歷史理解比喻為「意象」或「知覺」(包括直接與歷史接觸的感覺),並主張「歷史研究與藝術創作的共同點,在於形塑圖像的模式」。之後,他把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用視覺術語形容為「馬賽克法」(the mosaic method)。赫伊津哈在他的自傳中坦承,他對歷史的興趣是在童年收集硬幣時激發的,他之所以受中世紀吸引,是因為他想像那個時期是「滿是戴著羽飾頭盔的驍勇騎士」,而他之所以從東方研究轉移到尼德蘭歷史,則是受到一九O二年在布魯日的一場法蘭德斯繪畫展所啟發。赫伊津哈也是歷史博物館的強力倡導者。
赫伊津哈同時代的另一名學者瓦堡,一開始是個布克哈特風格的藝術史學者,最後他的專業則在於企圖建立起一套以圖像和文字兩者為基礎的文化史。由瓦堡圖書館發展出的瓦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在希特勒崛起之後從漢堡遷到倫敦,自此便一直不斷鼓勵著這樣的研究方法。因此,一九三O年代起開始頻繁造訪瓦堡研究所的文藝復興歷史學者法蘭西絲.葉茨(Frances Yates,1899–1981)便形容自己是被「傳授了瓦堡的技術,以視覺證據作為歷史證據」。
在一九三O年代,來自巴西的社會史學者吉爾貝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1900–1987)也運用了圖片與照片的證據,他把自己形容為提香(Titian,約1485–1576)風格的歷史畫家,而他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則是「印象主義」的形式,因為他「試圖在動作中為生命帶來驚奇」。另一名研究巴西的美國歷史學者羅伯特.萊文 (Robert Levine)也追隨弗雷雷的路線,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的拉丁美洲生活照片,他所附加的評註不僅將這些照片置放在其脈絡下,同時也討論了由於使用這類證據所引發的主要問題。
對於自稱為「週日歷史學者」的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2)而言,圖像是他兩項重要研究的起點,童年史與死亡史,視覺資料在這兩項研究中都作為「感性與生命的證據」,和「檔案庫中的文學和文獻」是一樣的基準。阿利埃斯的著作在稍後的章節會再詳細討論。一九七O年代,一些主要的法國歷史學者仿效了他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研究法國大革命及革命前舊政權的米歇爾.沃維爾(Michel Vovelle),以及專長十九世紀法國的墨西斯.阿古隆(Maurice Agulhon)。
美國評論家米謝爾(W. J. T. Mitchell)所稱的這種「圖像轉向」(pictorial turn),於英語世界中同樣可見。如他所承認的,在一九六O年代中期,塞繆爾和一些同時期的人開始意識到照片的價值,作為十九世紀社會史的證據,照片幫助他們建立起一部著重在一般人日常生活和經驗的「人民史觀」(history from below)。然而,若以深具影響力的期刊《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作為英語世界中歷史書寫的新潮流代表,卻令人訝異地發現,從一九五二到一九七五年之間,沒有一篇刊登的文章附有插圖。一九七O年代,期刊上刊載了兩篇配有插圖的文章。另一方面,到了一九八O年代,這樣的文章數目增加到十四篇。
就這方面而言,一九八O年代是個轉戾點,一九八五年所舉辦的一場美國歷史學者研討會紀錄也意味著這點,這場會議是關於「藝術的證據」。會議的論文集發表在《跨學科史學期刊》(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的特刊上,由於受到許多關注,因此這部論文集很快便重新發行為書籍形式。從那時起,其中一名論文作者西蒙.沙瑪(Simon Schama)更由於他在研究中使用視覺證據而為人所知,包括從十七世紀荷蘭文化的探討《財主的尷尬》(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1987),到數世紀來西方對風景畫態度的研究《風景與記憶》(Landscape and Memory,1995)。
一九九五年開始發行的這個「描繪歷史」(Picturing History)系列本身,包括你正在閱讀的這本書在內,也是這種新潮流進一步的證據。而新一代的歷史學家一直接觸著電腦和電視,他們實際上從出生起便始終居住在一個圖像滲透的世界,在接下來的幾年,觀察他們將如何處理過去的視覺證據,這會是件很有趣的事。
資料來源和軌跡
傳統上,歷史學者把他們的文獻稱為「資料來源」,彷彿他們正從「事實」的溪流中盛滿水桶,而隨著他們越靠近源頭,他們的故事就變得越來越純粹。這個譬喻很鮮明,但也可能有點誤導,因為它暗示著一種可能性,也就是一段關於過去的敘述可以不受中介物所污染。當然,研究歷史不可能沒有一整串中介物的輔助,其中不僅包括早期的歷史學者,還有那些整理文獻的檔案管理員、書寫文獻的抄寫員,以及話語被記錄下來的見證者。一如荷蘭歷史學家胡斯塔夫.雷尼爾(Gustaaf Renier,1892–1962)在半個世紀以前所建議的,若用目前存在的過去「軌跡」一詞,取代「文獻來源」的概念,這或許會有幫助。「軌跡」一詞可以指涉到手抄本、印刷書及、建築物、傢俱、風景(經過人類開採而改變),以及各式各樣的圖像:繪畫、雕塑、版畫、照片等。
歷史學者對圖像的使用,不能也不該侷限於「證據」一詞的嚴格意義上(如在第五、六和七章特別詳細討論的)。哈斯基爾所謂的「圖像對歷史想像的影響」也應留有空間。繪畫、雕塑、版畫等等使我們這些後代能夠分享過去文化中非語言的經驗或知識(例如下面第三章所討論的宗教經驗)。它們將那些我們先前已知但並未認真對待的部分,直接為我們送上門來。簡言之,圖像使我們能夠更加鮮明地「想像」過去。正如評論家斯蒂芬.班恩(Stephen Bann)所言,我們和圖像面對面的位置,也將我們帶往「與歷史面對面」。不同時期的圖像使用,例如作為虔敬的對象或勸說的手段、作為傳遞資訊或帶來愉悅,都使它們得以成為過去宗教、知識、信念、娛樂等等形式的見證者。雖然文字也提供了寶貴的線索,但對於過去文化中宗教與政治生活的視覺再現,圖像本身是最好的指引。
因此,本書將探究不同類型的圖像使用,如同律師們就不同歷史類型所稱的「可接受證據」(admissible evidence)。這個法律的類比是有道理的。畢竟,在過去幾年中,銀行搶匪、足球流氓和暴力警察都因為錄影證據而遭受判決。犯罪現場的警方照片經常當作證據使用。在一八五O年代,紐約警局製作了「罪犯照片集」(Rogue’s Gallery)以供指認竊賊。確實,在一八OO年以前,法國的警方紀錄已經在重大嫌犯的個人檔案中納入肖像畫。
本書的基本命題在於,試圖支持並說明圖像就像文字與口述見證一樣,是歷史證據的一種重要形式。它們記錄了目擊的動作。這不是什麼新的概念,倫敦國家藝廊的一幅知名圖像正說明了這點,也就是人稱「阿諾菲尼肖像」(Arnolfini portrait)的夫妻肖像。這幅肖像上題著「范艾克曾在此」(Jan van Eyck fuit hic),彷彿畫家當時是這對新人的婚禮見證人。恩斯特.貢布里希 (Ernst Gombrich)曾寫過「目擊原則」(the eyewitness principle),換句話說,就是自古希臘開始,某些文化中的藝術家一直遵循的規則,用以再現一名目擊者在特定的某時某地所能見到的事物——也只再現這件事物。
類似地,在一份關於維托雷.卡帕齊奧(Vittore Carpaccio)及一些同時期威尼斯畫家的畫作研究中,也引入了「目擊風格」(the eyewitness style)一詞,指的是這些繪畫中展示出對細節的熱愛,以及藝術家與贊助者渴望看到「根據證據的普遍標準,看起來盡可能忠實的畫作」。文字有時更加強我們的印象,認為藝術家關心的就是提供準確的見證。例如,美國畫家伊士曼.約翰遜(Eastman Johnson,1824–1906)的《為自由奔馳》(Ride for Liberty,1862)呈現三名馬背上的奴隸,男人、女人和孩子,在這幅畫作背後的題詞中,他將自己的畫作形容為「內戰的一場真實事件紀錄,是我親眼所見」。「紀實」(documentary)或「民族誌」風格等詞語,也用來描述之後類似圖像的特色。
不用說,圖像證據的使用引發了許多糟糕的問題。圖像是無聲的證人,很難把它們的見證轉譯成文字。它們的目的可能是傳達自身的訊息,但歷史學者們反而經常忽視,因為他們企圖讀出圖畫中「字裡行間」的意義,並且學到一些藝術家並不知道自己正在傳授的東西。這樣的過程中有著明顯的危險。若要安全地使用圖像的證據,先別說有效地使用了,就有必要了解其中的缺點——就和其他類型的資料來源一樣。書寫文獻的來源批判(source criticism)早已成為歷史學者訓練中的基本部分。相較之下,對於視覺證據的批判仍未發展成形,雖然圖像的見證就像文字見證一樣,會引發關於脈絡、功能、修辭、回憶(無論是事件發生不久或是很久以後),以及第二手見證等等的問題。因此,有些圖像會比其他圖像提供更可靠的證據。例如直接寫生的草圖,由於不受「宏大風格」(grand style,於下面第八章討論)的限制,它們作為證據時,比事後在藝術家工作室裡加工的繪畫更加可信。在歐仁.德拉克羅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的例子中,他的草圖《兩名坐著的婦人》(Two Seated Women)和他的繪畫《阿爾及爾的女人》(The Women of Algiers,1834)之間的對比或許正說明了這點,後者看起來較為戲劇化,並且指涉著其他的圖像,和原始草圖並不相同。
圖像會以什麼樣的方式提供關於過去的可靠證據,又能提供到什麼程度呢?對這樣的問題,若企圖得到一個簡單廣泛的答案,顯然是件愚蠢的事。一幅十六世紀聖母瑪利亞的聖像和一幅二十世紀史達林的海報,兩者都會告訴歷史學者一些關於俄國文化的事,但儘管有些饒富趣味的相似度,這當中還是有著明顯的巨大差異,這些差異既在於這兩幅圖像告訴我們的事,也在於它們所忽略的事。我們冒著風險,忽略了圖像的多樣性、藝術家、圖像的使用,以及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對圖像的態度。
圖像的多樣性
本文是關於「圖像」而不是「藝術」,西方世界直到文藝復興的進程時才開始使用這個詞,尤其是從十八世紀開始,因為至少在菁英階層中,圖像的美學功能開始主導了這些物件的許多其他用途。若不論美學品質的話,任何圖像都可能作為歷史證據所用。地圖、帶有裝飾的盤子、奉獻物、時尚玩偶,以及早期中國皇帝陵寢裡埋葬的兵馬俑等,全都有話要對歷史學生訴說。
更複雜的是,我們還必須考量到出現在特定時間地點中的這類圖像變化,尤其是在關於圖像製作的兩次革命時期,第一次是十五與十六世紀印刷圖像的興起(木刻、雕版、蝕刻等等),第二次是十九與二十世紀攝影圖像的興起(包括電影電視在內)。若要詳細分析這兩場革命的影響,會需要一本大部頭著作,但幾項一般性的觀察可能也同樣有用。
例如,圖像的外觀改變了。在木刻和攝影的早期,都是黑白影像取代彩色畫作。稍微推測一下,就像從口述訊息轉變到印刷訊息的情況一樣,有人可能會認為,用麥克魯漢知名的句子說,和更具幻覺效果的彩色圖像相比,黑白圖像是種更「酷」的溝通形式,能夠使觀者一方產生更大的疏離感。同樣地,就像晚期照片一樣,印刷圖像能夠比繪畫更快速地製作與傳播,因此當前事件的圖像能夠在事件記憶猶新的時候便傳到觀眾眼前,這點將在第八章繼續發展。
在這兩場革命的例子中,應該記住的另一個重點是,它們都使一般人能夠接觸到的圖像數量獲得了飛躍性的增進。確實,如今已難以想像,中世紀時一般流通的圖像有多稀少,因為我們如今在博物館或複製本中所熟悉的手抄本當時都在私人手中,只有祭壇畫或教堂壁畫能讓一般大眾看見。這兩次大躍進造成了怎樣的文化影響?
在印刷的影響上,人們經常就其中永久形式的字體標準化及固定化的方面討論,而印刷圖像可能也有類似的要點。小威廉.艾文斯(William M. Ivins Jr,1881–1961)是紐約的一名版畫策展人,他提出了十六世紀版畫的重要性,認為它們是「完全可重複的圖像陳述」。艾文斯指出,以古希臘人為例,他們放棄了替植物學專著製作插圖的做法,因為要在同一部著作的不同抄本中,為同一株植物製作相同的圖像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自從十五世紀後期起, 人們便開始固定以木刻版畫製作藥草的插圖。而從一四七二年開始印製的地圖則是另一個例子,這種和印刷相關的可複製性,在此加速了圖像帶來的資訊傳遞。
根據德國馬克斯主義評論家瓦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一九三O年代一篇知名文章中的看法,在攝影時代,藝術品改變了它的性質。機械「以多數的複製取代了獨一的存在」,並且將圖像的「崇拜價值」(cult value)轉換為「展示價值」(exhibition value)。「在機械複製時代所衰退的是藝術品的靈光。」人們可能會對這篇文表示懷疑,實際上也已有人提出。舉例而言,一幅木刻的主人可能會認真把它視為一幅個別圖像,而不是許多幅當中的一件複製品。有些視覺證據,例如在十七世紀荷蘭屋舍與旅館的繪畫中,便顯示木刻與雕版版畫就像畫作一樣展示在牆上。如同邁克爾.卡米兒(Michael Camille)所主張的,在較近期的攝影時代中,圖像的複製實際上可能正加強了其靈光——正如重複的照片增添了電影明星的丰采,而不是從中奪取。若說我們不像前人那樣認真地對待個別的圖像,儘管這點仍需證明,但即使真是如此,這很可能並非複製本身的結果,而是由於越來越多的圖像在我們的經驗世界中造成的飽和。
「開始研究事實前,先研究歷史學者,」知名教科書《歷史是什麼?》的作者如此告訴讀者。類似地,我們也可以建議,任何人若打算使用圖像的見證,就先研究其製造者的不同目的。舉例來說,那些主要用來做紀錄的作品就相對可靠,比如用來紀錄古羅馬遺跡,或是異國文化外觀或風俗的作品。例如,伊莉莎白女王一世時代的藝術家喬恩.懷特(John White,活躍於1584–93)筆下的維吉尼亞印地安人圖像就是現場寫生的,一如那些跟隨庫克船長和其他探險家的製圖者,他們所繪的夏威夷與大溪地居民的圖像,正是為了記錄他們的發現。那些被送到戰場上的「戰爭藝術家」,是為了描繪戰爭與士兵的生活(第八章),他們活躍的歷程從查理五世皇帝遠征突尼斯起,直到美國干預越南的時期,如果沒有更晚的話。比起那些完全在家工作的同行,他們通常是更為可靠的見證者,尤其在細節方面。我們可將此段所列的這類作品形容為「紀實藝術」。
儘管如此,若認為這些藝術家記者擁有「純真之眼」,意即完全客觀、不帶任何類型的期待或偏見的目光,這就不夠明智了。就字面意義和譬喻意義兩者而言,這些草圖與繪畫都記錄了一種「觀點」。在懷特的例子中,我們必須記住他個人和維吉尼亞的殖民化有關,於是他可能會試著提供對這個地方的好印象,例如忽略掉那些裸露、人類獻祭,以及任何可能會嚇到潛在移民者的景象。使用這類文獻的歷史學者絕不能夠忽略其中宣傳的可能性(第四章),或是對於「他者」的刻板觀念(第七章),或是忘記在特定文化或在特定類型中,例如戰爭畫作(第八章),那些人們習以為常的視覺慣例所具有的重要性。
為了支持這種對純真之眼的批判,我們不妨舉出幾個相對上清楚直接(或至少看來是如此)的圖像歷史見證作為範例:照片與肖像。
延伸內容
【國際好評】
「徹底引人入勝的解釋,告訴讀者如何能夠將美術、圖形、照片、電影與其他媒材用在理解其他時代的生活方式。」——《泰特雜誌》(Tate Magazine)
「知識淵博、見地公正,且發人深省。」——邁克爾.巴克桑德爾(Michael Baxandall),《英國歷史評論》(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歷史的目擊者》完全不是在講圖像的價值,而是在講文字的首要性……在許多脈絡中,圖像若少了文本的輔助就不具意義,而透過不斷引用這些脈絡,本書對於保存那些以文本為主的舊式風格歷史,提供了持續的論證支持。」——尼可拉斯.海利(Nicholas Hiley),《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柏克……描述且評估了傳統上藝術史學者用來分析圖像的方法,指出它們不足以表述視覺圖像的複雜度。」——《圖書消息》(Book News)
「柏克……研究的是圖像作為歷史證據的來源,他因此寫出了一本好書……眾所周知,作者……感興趣的是找出語言、文化與時代之間的連結,還有方法學和學科之間的連結。本書是這種廣泛智慧運作的實例,是歷史、文化、美術、人類學與電影學生的必讀書目。」——《選擇》(Choice)
「在圖像作為歷史研究的諸多範例方面,以及對關鍵概念與理論的清楚總結方面,本書別具價值……《歷史的目擊者》強烈推薦給歷史學者以及藝術史學者。」——妮娜.史蒂芬森(Nina K. Stephenson),新墨西哥大學,《藝術文獻》(Art Documentation)
「任何一名戒慎的歷史學者讀到這本書時,光想到圖像用作證據都會心驚膽顫。柏克在研究歷史學者可能使用的這類圖像時,同時詳述了這些陷阱……總而言之,針對一項棘手主題,這是一部令人振奮的簡短引介。」——《維吉尼亞評論季刊》(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一如彼得.柏克在《歷史的目擊者》中所闡明的,圖像有著扭曲事實的悠久傳統。那麼,圖像對於歷史學者來說有何作用呢?圖像提供的是何種類型的歷史證據呢?柏克著手回答這些問題。他的著作企圖鼓勵並指導讀者在歷史編纂上使用圖像,而本書在兩方面都相當成功……透過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研究,柏克向歷史學者展現了圖像的價值,同時也對圖像使用提出有益的警告……對那些新接觸圖像研究的人而言,《歷史的目擊者》為視覺文化在歷史編纂上的使用,提供了容易進入的實用介紹。而對於那些已致力視覺現象研究的藝術史家與學者們,柏克的著作能夠有力地提醒圖像與歷史之間的複雜關係。」——莎朗.科爾溫(Sharon Corwin),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科技與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編輯推薦
【編輯推薦】圖證歷史的所見與未見
《歷史的目擊者》是英國著名史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的作品,他是位產量極大的新文化史家,外界的翻譯速度往往趕不上他的新書出版,台灣也是在二○○三年之後,就不見他的譯作,此書是睽違近二十年後的柏克的繁中作品。
本書獲各界主流媒體,包括《泰晤士報文學副刊》、《藝術與文獻》、《技術與文化》等,在全球更授出超過10國外語版權。
本書提出有關圖證歷史的論述,假為真,真為假,圖證歷史不是一場關於是否該使用圖像為歷史證據的辯論,更是關乎該如何使用。柏克跨地區、跨時期、跨傳播媒介研究多種圖像,從貝葉掛毯,到宗教圖像、政治圖像、廣告圖像、商品圖像……深入且全面鑽研圖像的實際用途。
同時,柏克也提出摘要式的指引,在本書中收錄的新版序言中,他稱之為「十誡」。搭配書中名家作品或文句,有脈絡地教導讀者如何從圖像中剖析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了解背後隱含真義,並避免錯誤解讀的陷阱。更多編輯推薦收錄在城邦讀饗報,立即訂閱!GO
作者資料
彼得.柏克 Peter Burke
英國歷史學家。1937年生,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學士、聖安東尼學院(St Antony’s College)碩士。曾任莎賽斯大學(Sussex University)高級講師、劍橋大學文化史高級講師,現任劍橋大學文化史教授及伊曼紐學院(Emmanuel College)研究員。 柏克的研究專長在歷史思想領域、1450至1750年的歐洲文化史,以及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著作包括:《1420至1540年間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文化與社會》(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 1420-1540)、《近代歐洲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社會學與歷史學》(Sociology and History)、《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89》(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製作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大眾傳播媒體的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網際網路》(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 from Gutenberg to the Internet)等書。注意事項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