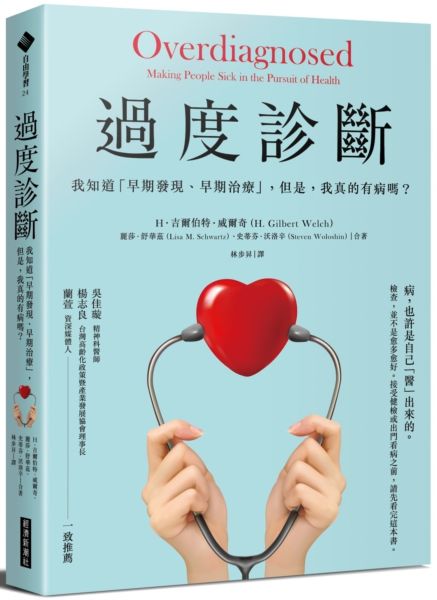【前言】
◎文/H.吉爾伯特.威爾奇(H. Gilbert Welch)
我們的診斷狂熱
我生平第一輛車是一九六五年出廠的福特費爾蘭(Fairlane)旅行車,車身雖大但結構單純,有些維修工作我甚至能自己完成。引擎蓋底下空間很大、電子零件很少,油溫表和油壓表是唯二的引擎感知器。
至於我那輛一九九九年出廠的富豪(Volvo)可就截然不同了:引擎蓋下塞滿電子零件、沒有多餘空間,還有許多小型警示燈偵測車子各式各樣的功能,因此這些警示燈全都得連接至內部電腦,才能判斷何處故障。
從小到大,我見證了汽車的成長,不但較以往更加安全、舒適和可靠,工程設計也更為優異,只是不曉得這些進步跟那些警示燈有多大的關係。
引擎警示燈變得愈來愈精密。這些警示燈假如亮起,代表車輛可能出了問題,因此能遠在車輛性能受影響前測得異常,等於進行早期診斷。
你的引擎警示燈也許幫過大忙,提醒你去做重要的事(像是加油),進而避免日後產生更大的問題。
說不定你的經驗正好相反。
引擎警示燈也可能帶來問題,有時根本是虛驚一場(每次我開車壓過減速丘,就會有個警示燈亮起,提醒我冷卻系統出了問題)。通常,這類警示燈是真的發現異常才會亮起,但多半都不是特別要緊的問題(最好玩的是能偵測其他感知器是否失靈的警示燈)。最近,我的修車技師私底下告訴我,許多亮起的警示燈應該可以不予理會。
也許你決定要忽視這些警示燈,或早已把車子拿去維修,而技師只是恢復原廠設定,叫你再觀察燈是否又莫名亮起。
或者你倒楣到花錢把車送修,結果卻證明毫無必要,或花了好多次冤枉錢;又或者你真的衰上加衰,車子反而愈修愈爛。
若是如此,那你對過度診斷的問題已有些體悟了。
我不曉得這些警示燈的整體效用為何,可能利大於弊、也可能弊大於利。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對汽車維修業絕對有所影響,即前往維修廠成了家常便飯的事。
我也知道,若我們這些醫生檢查得夠仔細,很可能會發現你的身體某處亮起紅燈。
►定期檢查
我自己的身體很可能就亮了一些紅燈。身為五十多歲的男性,我成年後就沒再到醫院做定期健康檢查了。這並不是在自吹自擂,也不是要其他人效法。但由於我有幸受老天眷顧,一直以來都身強體壯,因此也很難說我少做哪些必要的檢查。當然,身為一名醫生,我每天都會看到很多同行,其中不少都是我的朋友(至少他們在得知本書前沒跟我絕交),假如我是他們門診或自己門診裡的患者,不難想像會得到以下的診斷結果:
● 我的血壓會三不五時偏高,上班期間量血壓尤其如此(血壓計容易取得)。
診斷:臨界性高血壓● 我的身高195 公分、體重93 公斤,身體質量指數(BMI)是25。(「正常」BMI 值範圍是20 到24.9 之間。)
診斷:過重
● 有時在飲食過後,我的胸口會感到灼熱難耐(蘋果汁和蘋果西打帶來的不適感尤其嚴重)。
診斷:胃食道逆流
● 我經常會半夜醒來上廁所。
診斷:良性攝護腺肥大症
● 我早上起床往往關節僵硬,都要好一陣子才能放鬆。
診斷:退化性關節炎
● 我的雙手容易發冷,而且是真的冰冷,滑雪或雪地健行時造成的問題可大了,但辦公室裡也會發生(問我的患者就知道了)。喝咖啡會讓症狀惡化,喝酒則能有助減輕症狀。
診斷:雷諾氏症
● 我必須把待辦事項列成清單才記得住,還時常忘記人名,學生的名字忘得特別快。我也得記下所有的個人識別碼(PIN)與密碼(假如有人需要,去我電腦裡查就好)。
診斷:早期認知障礙
● 我家的馬克杯都固定擺在一個架子上,玻璃杯則固定擺在另一個架子上。內人不明白這個邏輯,每次由她把洗碗機的杯碗拿出來放,我必定得把所有東西重新歸位(小女從不幫忙清空洗碗機,但那是另一回事了)。我上班穿的襪子、跑步穿的襪子、冬天穿的襪子都有各自的收納空間,而且必須成雙成對排好才會收起來(這類例子不勝枚舉,多到你不會想知道)。
診斷:強迫症
好啦,我承認自己有點天馬行空了。我認為不會有人對我做出精神疾病相關的診斷(至少我直系親屬以外的不會如此),但只要看診時仔細詢問,再測量簡單的數值(例如身高、體重和血壓),確實可能做出前幾項診斷。
如果醫生指示要進行其他檢驗,就可能做出更多診斷。即使是血液常規檢查(完整血球數值、電解質組合與肝功能指數)都包含二十多項獨立的數值,我很可能至少有一項數值異常。
另外還有造影檢查。許多人會在X 光檢查報告發現「異常」。倘若我接受胸部X 光檢查,照出肺部有個結節,我並不會感到訝異;若我去做腹部電腦斷層檢查,結果發現腎臟有顆囊腫,我也不會覺得意外。
再進一步的檢查,說不定會發現更多毛病。結腸內視鏡檢查後,可能會發現我腸內有息肉,畢竟同年齡層約三分之一有此問題。攝護腺切片檢查結果則可能發現少許癌細胞,許多男性即使攝護腺特異抗原(Prostate-specific antigen,PSA)篩檢結果正常也會罹患此癌。而我的基因體八成也有各式各樣的基因變異。
平心而論,多數醫生都不會要求造影檢查,說不定連血液常規檢查都予以省略,但仍可能做出上述其中幾項診斷。
假如我被診斷出這些症狀,健康會有所改善嗎?我不覺得。我會不會拿到處方箋?很有可能。這樣的醫療服務好不好呢?我會說不好。但先別管我了,本書關注的對象是數百萬名美國人,他們享有不少人口中全球一流的醫療服務。當然,還有數百萬名美國人由於缺乏醫療險,因此受到的保障嚴重不足。這固然是現實的問題,但不是本書的主軸。而且正因為這群人的醫療資源有限,反而不大容易受到書中所列問題影響。本書探討的是醫學過度發達,以及我們愈來愈輕易做出診斷的傾向。
美國人向來都訓練有素,懂得重視自身的健康。我們身體潛伏著各式各樣的隱疾。傳統觀念都認為,我們與其渾然不覺地過日子,不如對這些隱疾有所覺知,進而採取相應對策,而且愈早發現愈好。因此即使我們自認健康,依然熱衷於種種能檢測出異常的先進醫療技術,也因此我們喜歡找出危險因子、樂見疾病防治宣導、接受癌症篩檢與基因檢測。美國人就是愛給醫生診斷,尤其是早期診斷。
毫不意外的是,現今我們得到的診斷數量已超越過去。實際上,我們正處於診斷泛濫的時代。傳統觀念也指出這個趨勢是件好事:及早發現問題才能拯救生命,這樣就有機會「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我們甚至相信,找出身體的毛病完全有利無弊。
但實情是早期診斷宛如一把雙面刃,確實有可能幫助部分患者,但絕對有一項潛在的危險,那就是過度診斷,也就是說,檢測到的異常絲毫不會影響健康。
►長壽卻不健康?
想想看,跟我同輩的人都屬於嬰兒潮世代,即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生育率的高峰期,日後陸續引領了一九六○年代多項重大社會運動,包括黑人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和反越戰示威,也催生了那個時代的反主流文化:性、毒品和搖滾樂。他們長大成人後,自己便成了主流文化,不但取得政治權力,也累積了巨大財富。
如今,許多電視廣告打造出退休生活的全新願景,讓他們可以持續追求夢想,譬如阿默普萊斯金融公司(Ameriprise)的廣告中,已故男星丹尼斯.霍柏(Dennis Hopper)說:「我真不覺得你會甘願玩推盤之類的無聊遊戲,懂嗎?」(背景那震天價響的音樂,是經典搖滾金曲〈給我一些愛〉〔Gimme Some Lovin’〕撼動人心的樂句)高中時期的美好回憶再度浮現,我很愛那首歌。
然而,我後來在《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讀到一篇文章指出,嬰兒潮世代的確得做好準備,退休生活可能跟想像的截然不同(來源:Rob Stein, “Baby Boomers Appear to Be Less Healthy than Parents,” Washington Post, April 20, 2007.)這是因為他們的健康拉起警報。多項大型全美調查顯示,二戰前出生且屆齡退休的民眾之中,57% 自認身強體壯,但嬰兒潮世代只有50% 如此認為;二戰前出生的民眾之中,56%表示在退休時已有慢性疾病,但同年齡的嬰兒潮世代,慢性疾病的比例達到63%。難道嬰兒潮世代的身體比自己的父母還差嗎?
幾週後我出席了一場醫學會議,其中一位與會者報告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針對《二○一○健康國民白皮書》(Healthy People 2010)的期中評鑑結果。這項計畫是由聯邦政府推動,目的在延長壽命、促進生活品質。壽命的長短是以平均餘命來衡量,即目前美國人的平均壽命;生活品質則是以健康平均餘命來衡量,即美國人處於健康狀態(沒有罹患心臟病、中風、癌症、糖尿病、高血壓和關節炎等疾病)的平均壽命。該講者亮出彙整一九九九年至二○○二年資料的表格,顯示平均餘命從76.8 歲增至77.2 歲,多了六個月,但健康平均餘命居然從48.7 歲減至47.5 歲,少了超過一年。
由此看來,該計畫的目標只達成一半:壽命本身確實正在延長(民眾活得更久),但健康壽命卻隨之減少(民眾無病無痛的日子減少)。難道我們活得長壽卻犧牲健康了嗎? 這實在讓人難以置信,但還有另一項可能:我們活得更久也更健康,只是愈來愈容易讓人告知自己生病了。
有些人可能認為,多診斷(與多治療)是提升平均壽命必須付出的代價;這項看法的前提是,唯有早期診斷和治療可以保障延年益壽。但由於其他因素更為重要(譬如不抽菸、充分營養、重症醫療等),因此很可能無論診斷的多寡,平均壽命依然會增加。況且對許多人來說,壽命長短不是唯一目標,當前更需要研究的問題是:當前醫療體系是否帶來更多的疾病與失能?
►關於本書
家母自認了解這本書的內容。年近九十歲的她嚴重失智。幾個月前,她拿起我寫的第一本書,大聲讀出書名:「我應該接受癌症篩檢嗎?(英文書名是 Should I Be Tested for Cancer?)」隨後語氣堅決地回答:「當然不要!」(小叮嚀:她的回答堪稱本書內容的極度精簡版。)
當時,她問我下一本書的內容為何。我便試著解釋給她聽,她建議書名取為「我應該接受疾病篩檢嗎?」雖然這個書名不大響亮,但至少讓你有個概念。本書探討的是,美國醫學界是否把太多人貼上「生病」的標籤。
如前所述,傳統看法是愈多的診斷(尤其是愈早確診)就有愈好的醫療照護,背後邏輯約略等於:愈多的診斷代表愈多的治療,而愈多的治療愈能促進健康。對某些人來說也許確實如此,但從另一面來看,診斷數量的上升可能讓健康的人更加沒安全感;而且說來諷刺,還可能危害健康。而且過多的診斷會導致過多的治療,即治療那些不太礙事或毫無影響的症狀。
當然,過多的治療真的可能造成傷害;基於過多診斷而進行的治療,說不定比疾病本身更可怕。
更確切來說,本書探討的是過度診斷,聽起來只是「過多的診斷」,但其實有更精確的定義:所謂的過度診斷,係指診斷出的病況並不會引發任何症狀或導致死亡。
因此,我在前幾頁中自行診斷出一些病況中,有些並不屬於過度診斷,因為我的確有胸口灼熱、雙手冰冷等等症狀(不過也可能是過多的診斷,畢竟症狀都算輕微)。但血壓與體重偏高之類的診斷不牽涉任何症狀,可能就有過度診斷的疑慮;而我在接受後續檢查後得到的所有診斷,同樣可能是過度診斷。換句話說,唯有醫生在患者毫無相關的症狀時做出診斷,才可能出現過度診斷的情形。
儘管醫生在評估不相關病況的過程中,也可能意外做出過度診斷,但造成過度診斷的主因,通常是組織篩檢或定期檢查時,醫生設法進行早期診斷。因此,過度診斷是對於早期診斷熱衷的結果。
問題在於,除非當事人自願放棄治療、毫無症狀地度過餘生,最後出於其他原因死亡,否則我們醫生無從得知患者是否遭到過度診斷。但可以確定的是,若我們針對健康民眾的診斷愈來愈多,就更可能做出過度診斷。
過度診斷在醫學界是相對近期的問題。過去,民眾身體健康時不會看醫生,通常等到症狀出現才會看病。此外,醫生也不鼓勵健康的民眾看病,結果就是以前醫生做出的診斷比現在少。
但這樣的思維模式已有轉變。早期診斷成為目標,民眾即使健康也要看病,醫生設法及早找出疾病。愈來愈多人在疾病初期就檢查出來。於是,我們做出更多診斷,包括診斷根本沒有症狀的人,有些人必定會出現症狀,有些人則沒有任何症狀,這就是被過度診斷的一群人。因此,過度診斷的問題直接源於受到診斷人數的增加,包括確定有症狀的患者,以及無症狀僅有異常的民眾。而隨著「異常」的定義愈來愈廣泛,這個問題也就愈來愈嚴重。
本書目的是列出各項資料,指出過度診斷如何發生、何以可能導致危害並且深究問題的根源。我希望幫助你運用批判能力,思考過早遭人判定成患者是否妥當。
容我說明為何你應該關注過度診斷的問題。因為醫生無從得知哪些人是過度診斷,所以遭受過度診斷的患者往往會接受治療。但對於這些患者沒有任何好處,畢竟本來就沒東西可醫(既不會出現症狀又不會死於病況),因此根本不需要治療。過度診斷只會適得其反。真相簡單明瞭:幾乎所有治療都可能造成危害。
►非關本書
本書不會告訴你生病時該怎麼辦,也不是寫給少數亟需醫療的重症患者,而是寫給目前(或曾經)健康無虞的多數民眾,與只罹患單一疾病、恐被診斷出其他疾病的人。本書也無意為粗心的診斷結果道歉。對於飽受病痛所苦的人,診斷確實無比重要,而且必須做得精準到位。無論在本書中讀到任何看法,請勿解讀成生病時不給醫生診斷較好。
最後,本書並非在譴責整個美國醫學界,也無意鼓吹民眾尋求另類療法。我自己是西方傳統醫學訓練出身,也認為醫生對社會有莫大的貢獻。假如你生病了,請乖乖看醫生。
►最後說明:名字與語言
進入正文之前,我覺得有必要針對書中名字與用詞稍加說明。本書有許多故事,可能是關於我的患者、朋友或一路上遇到的人。這些故事內容全都屬實,但名字都有所改變。我沒更動臨床紀錄相關的資訊(例如性別、年齡、症狀和經歷),但修改了可能足以認出個人的資訊(例如對方來自紐約或紐澤西,小女八成會說:「最好這很重要啦!」)。
再來就是「疾病」(disease)一詞。這個詞彙有各式各樣的意思,但字源其實十分精確:字首「dis」意為「沒有」,字根「ease」(舒適)更不必解釋。「disease」有個同義詞是「discomfort」(不適)。雖然該詞彙還有其他完全合理的定義,本書凡是提到「疾病」,都是指患者主觀感受的病況,即會產生症狀的疾患或失調。
「異常」(abnormality)一詞則有不同的用意。我會用這個詞彙來形容醫療專業人員判定的結果,但患者本身卻無主觀感受。有些再熟悉不過的異常(像是高血壓和高膽固醇)有時會稱為病況,好跟疾病區隔。
我在書中偶爾會用「醫療照護人員」(health-care provider)這個籠統的詞彙,但為了簡潔起見,我往往會直接使用「醫生」一詞。這不是要排除其他照護人員,反而是正視醫師助理與專科護理師日益重要的角色,在一般醫療(primary care,另譯為基層醫療或初級照護)時尤其如此(此階段會做出許多診斷)。
最後,快速交代一下代名詞的使用。最常見的就是「他」(he)和「她」(she)。當然,患者可能是男性或女性,醫生也是如此(不過達特茅斯醫學院在學學生中,女性多於男性)。我沒找到一個滿意的方式,處理英文缺乏中性單數代名詞的問題。單純用「他」或「她」久了顯得彆扭,改用「they」(他/她們)又會惹得家母不開心。所以只要情況允許(部分疾病只限單一性別),我會把兩個代名詞交替使用。
然後是書中的「我們」(we),「我們」通常指的是「我們醫生」或「我們醫療照護人員」(我的「通常」意思是「大約九成的情況」,但我懶得去計算正確的機率)。我使用「我們」是要傳達醫生的專業觀點,包括我們在醫學院所學、住院醫生的訓練、行醫累積的經驗。簡單來說,我會設法讓你對我們的看法有所概念,這並不是說我們的看法必定一致,而是我們確實有共同的經歷,你應該對此有些理解。
有時「我們」指的是「一般民眾」,你我都是社會的一分子,隨時可能成為患者。我們所有人都會面臨相關抉擇,思考該如何跟醫療體系打交道。每當我有意傳達這項觀點時,就會把「我們」改成「一般民眾」。
「我」則代表我自己、作者,但其實也是另一個「我們」,因為本書其實是三位作者合著:麗莎.舒華茲(Lisa M. Schwartz)醫師、史蒂芬.沃洛辛(Steven Woloshin)醫師,以及我自己;但為了避免跟其他的「我們」混淆,才必須用「我」來巧妙替換。
在此也要特別說明,我們的聲音包含了二項觀點:我們三位作者都是跨足學術界的醫生,兼顧看診、教學與研究;但我們畢竟也是人,因此可能成為患者。身為一般人,我們十分憂心醫學的大肆擴張,從而讓許多人就此成為患者。正是上述醫學與個人二項觀點的融合,成為撰寫本書的動機。
 放入購物車
放入購物車 放入下次購買清單
放入下次購買清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