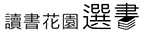- 庫存 = 7
 放入購物車
放入購物車 放入下次購買清單
放入下次購買清單
公雞之家:從被消失的家族成員追溯一個烏克蘭家族的百年離合,在尋找自我的碎片中回望邊境之國的記憶與哀愁
- 作者:維多利亞.貝林姆(Victoria Belim)
- 出版社:臉譜
- 出版日期:2023-03-28
- 定價:460元
- 優惠價:79折 363元
- 優惠截止日:2025年11月25日止
-
書虫VIP價:363元,贈紅利18點
活動贈點另計
可免費兌換好書 - 書虫VIP紅利價:344元
- (更多VIP好康)
本書適用活動
分類排行
-
心經超圖解:看圖就懂,史上最強般若智慧解析
-
多巴胺國度:在縱慾年代找到身心平衡
-
竹林姊妹:從中國到美國,雙胞胎拐賣、收養、離散的真實故事【作者印刷簽名扉頁版】
-
深夜裡的哲學家:為什麼好人總會受苦?人生有意義嗎?讓蘇格拉底、笛卡兒、尼采等70位大思想家回答45則令人深夜睡不著的大哉問
-
神經科醫師的名畫探案:美學×醫學×歷史的疾病探案之旅!偵探醫師解剖東西藝術珍品,自人物的表情、肢體、動作與感官線索,拆解神經疾病密碼
-
律師帶你看校園大小事: 老師和家長必知的44個霸凌防制和性平觀念指南
-
一分鐘秒懂漫畫易經:洞悉窮通順逆,通曉世事人情。原來易經這麼懂中國生存哲學,難怪南懷瑾、曾任強、季羨林這些大師都讀易經!
-
長女病:我們不是天生愛扛責任,台灣跨世代女兒的故事
-
香料(地中海史權威羅傑.克勞利歷史新作):以摩鹿加群島為中心,見證十六世紀形塑現代世界的權力地圖
-
她物誌:100件微妙日常物件裡不為人知的女性史
內容簡介
「我們家族應該對蘇聯感恩戴德。」
「我一向覺得懷舊是種病,對蘇聯的懷舊更是病入膏肓。」
當俄烏關係白熱化,
一場伯侄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引領作者回到烏克蘭外婆家的櫻桃園,
牽引出一個家族橫跨四代紛雜的歷史記憶與認同
★未出版即全球銷售16國版權★
★The Bookseller 當月選書★
★《鷹與心的追尋》作者海倫.麥克唐納推薦★
吳照中|「烏克蘭什麼」創辦人
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
房慧真|作家
洪美蘭│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教授
相振為|三立電視《消失的國界》資深記者
劉致昕|《真相製造》作者
——推薦
如今還在進行式的俄烏戰爭,近可回推至2014年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軍事行動,遠則可溯及俄羅斯及烏克蘭糾纏長達百年以上的歷史。也就是在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那一個歷史時刻,作者維多利亞‧貝林姆的電腦螢幕閃現著一則訊息:「我們家族應該對蘇聯感恩戴德。」而這訊息來自她曾因蒐藏披頭四唱片,在蘇聯統治烏克蘭時期鋃鐺入獄的伯父。
出生於烏克蘭的兩個世代面對同一場戰爭,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詮釋。對作者而言,蘇聯象徵的是車諾比核災、專制統治與大饑荒。對她的伯父而言,蘇聯不僅是核工程與航空科技的先鋒,更是保護烏克蘭免於納粹統治的軍事強權。
這場由著政治立場相左的爭執,以及曾祖父日記記下的一名失蹤家族成員,帶領作者回到離開十年以上的故鄉波爾塔瓦的櫻桃園。在塵封的照片、日記及藏書中,以曾祖父母所經歷的歷史事件為本,貝林姆走訪烏克蘭社會主義時代的祕密警察單位「公雞之家」、各地檔案室、博物館及祖厝,試圖拼湊不斷消失中的家族歷史,解開四個世代面對政權轉移的立場歧異及糾結。
「哀悼一個地方,比哀悼一個人還難。」曾經對作者而言,俄軍侵略克里米亞的新聞畫面,彷彿存在於老舊電影的灰色畫面。隨著一邊協助農務一邊穿梭於以列寧命名的無數街道,在破碎凌亂的檔案與歧異紛亂的歷史認同中,作者以一個家族的故事折射出一個「邊境之國」的歷史處境,並且在進行式的戰爭中,找回未經戰火蹂躪的烏克蘭,及一個家族重新找回連結的可能。
國內外好評——
早在2014年克里米亞被俄羅斯占領、頓巴斯戰爭開啟,種族問題及世代觀念上的落差,就在撕裂烏克蘭社會。而移居國外的作者,為了解開一個家族成員間難以啟齒的祕密,返回故鄉烏克蘭,踏上一段有如推理解謎般的旅程。對照身處台灣的我,因為類似緣由,也與作者有相同困擾。台灣與烏克蘭因地緣關係,有著許多難以避免的相似性。如果你也苦於台灣社會的分裂,相信作者的尋根之旅,能給你帶來不同視角的觀點。
——吳照中|「烏克蘭什麼」創辦人
既嚴肅又美麗地召喚出一個在危急存亡之秋的國度,也描述了作者個人如何設法尋回由家族跟國家所維護的回憶與祕密。這本書是對流亡、回歸與歸屬,乃至於對於人存在的意義,一次細緻的思索。最重要的,這本書是一首獻給希望與家的頌歌,其行文是如此地溫柔,對真實情感的堅持是如此深切,以至於對我來說,書中的字句化為了一種強悍的存在,供我擲向傷害、苦難、痛楚。這本書深得我心,它將縈繞在我的內心久久不去。
——《鷹與心的追尋》(H Is For Hawk)作者海倫.麥克唐納(Helen Macdonald)
目錄
自序
第一部:在烏克蘭的河岸邊
第一章:伯侄之間
第二章:尼科季姆怎麼了
第三章:重返貝里格
第二部:櫻桃園
第四章:復活節
第五章:魯許尼基
第六章:列舍季利夫卡
第七章:夜宿馬亞齊卡
第三部:刺繡的線頭
第八章:普拉頓叔叔
第九章:二訪列舍季利夫卡
第四部:公雞之家
第十章:哈爾科夫
十一章:字裡行間
十二章:尼科季姆的檔案
十三章:黑洞
第五部:洞窟與謎團
十四章:天上掉下來的親戚
十五章:鹽柱
十六章:和解
十七章:真相
結語
內文試閱
哀悼一個地方比哀悼一個人還難。失去深愛的人是悲劇,卻也是人生在世必經的過程,但戰爭則否。看見我們熟悉的地標陷入暴力殺伐,我們會哀慟於那個曾經的自己,也會質疑起自己變成了什麼。哀慟對我的擠壓,到了我再也無法把一個想法完整說出來的程度。有時候在跟三五好友共享一杯紅酒,我會猛然想起要是俄軍侵略到克里米亞以外的地方,那該如何是好?兒時那些二戰電影中的灰色畫面,在我的腦海中快速掠過:坦克開過我外曾祖父母的村落、身著迷彩服的男人將我們的櫻桃樹砍倒,炸彈落於我們在基輔的舊公寓上。朋友會問我還好嗎,而我會啜飲一口酒,然後點點頭。我不知道怎麼跟這些關心我,但戰爭於他們只存在於遠方跟報紙的朋友,解釋這場克里米亞不曾宣戰的戰爭每多打一天,我的內心就會多碎掉一點。在這種狀況開口尋求同情,就是在逼人做出道德判斷跟選邊站,連我自己都還沒能搞懂那些事件。
我的家人也各自用他們的方式在哀悼與陷入驚慌。我母親想像最糟糕的狀況,並舉了巴爾幹半島的例子解釋烏克蘭的狀況。我阿姨會跟看法與弗拉迪米爾類似的人解釋她的立場。她會抱怨她以前的同學對俄國總統的沉迷。「他還跑去買了一件跟普丁差不多的西裝外套。你知道,就是全黑然後有小硬領的那種,」她說。「每年他都會到俄羅斯一遊,以便能『呼吸自由的空氣』,至少他在臉書上是這麼寫的。他住加拿大耶。」在這些對話之後,我既有點想哭,又有點想捶牆。
我最常聊天的對象,是我的外婆瓦倫提娜,因為她不想聊戰爭。她說每天電視一打開跟每天一遇到人,都是戰爭戰爭戰爭,她累了。她主要聊的是果園跟春耕。我問她有沒有旅行護照,因為說不準我們會需要把她從烏克蘭疏散出來,她說她不需要。我堅持了一陣,她一字一字地重複說她就算是天塌下來,也哪裡都不去。還有就是跟瓦倫提娜說話,我不用擔心講錯話讓彼此不爽。
跟外婆聊櫻桃樹的修剪與番茄的種植,可以讓我忘記很多事情,但只要電話一掛上,就又會回到焦慮跟沮喪的狀態。我同時很放不下跟弗拉迪米爾的衝突。在腦中沙盤推演了很多種論述,希望能讓他相信蘇聯解體不是最大的災難,不解體才是。我想像跟他說烏克蘭以其位於俄羅斯與西歐間的關鍵位置,將永遠會是俄羅斯帝國野望的戰場,而俄羅斯將千方百計將這片土地控制在它的手裡,但烏克蘭人有權選擇由誰來統治他們,也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但這時我又會想起他那不公平的指控,憤怒不但回歸而且加倍。
即便如此,我還是找到了一件自己能做的事情。那就是買張機票前往烏克蘭。弗拉迪米爾曾拿這件事數落我,而我決定接受他的挑戰,讓他沒話說。就這樣在某天早上,我立誓要重返貝里格。
貝里格,或認真一點講叫作克魯提貝里格是我們給烏克蘭中部波爾塔瓦附近的村子取的名字。曾經,克魯提貝里格決定了一七○九年波爾塔瓦之戰的戰略,為歐洲歷史畫出了分水嶺,並靠養蠶織布興盛了起來,但那些光輝的事件早已成為過往。克魯提貝里格的意思是「陡峭的河岸」,顧名思義位於沃爾斯克拉(Vorskla)河畔,但如果把形容詞拿掉,貝里格一詞對我媽媽這邊的家族而言,代表著「我們的河岸」。
我母親的家族並沒有人生於此處,就連身為一家之長的外曾祖父母,阿絲雅與賽爾吉也不是。他們確實扎根在波爾塔瓦一帶,但貝里格只是他們對故土最接近的推測。他們沒有傳家的珠寶承襲自顯赫的祖先,也沒有成冊的家譜詳實記載一切。他們只知道自家的遠祖確實存在,但沒有留下太多的痕跡。住在一個有著「血腥之地」、「邊境之地」、「邊疆」等名號的兵家必爭之地,想累積恆產跟維繫一脈相傳的歷史談何容易。阿絲雅與賽爾吉歷經了二十世紀許多回的動盪,他們的生活方式也一次次被如海嘯一般的大事件給沖刷掉。到了最後,但凡在紛亂中能留下來的東西都會被當寶貝。我母親跟阿姨爭著阿絲雅一九三○年代的缺角杯組,那種熱情會讓你覺得是兩個希臘人討論要如何把額爾金大理石從英國手中要回來。即便只是一只透光的瓷器,它也站在memento mori,也就是「死亡紀念品」的對立面,它不像死亡紀念物那樣提醒著我們凡人必有一死。它成了一種vivere memento,也就是「生命紀念品」,扮演的是對生命與韌性的寶貴證詞。做為母親家族在戰爭的紛亂後倖存之地,貝里格成了我們家最重要的生命紀念品。
我生在基輔,但我生命的前十五個夏天都在這個沃爾斯克拉河邊的小村展開。貝里格是我第二個家,阿絲雅與賽爾吉是我的第二組爸媽。我在布魯塞爾的書架上放著他們的結婚照—一臉正經的兩個年輕人。他們看起來比較像準備好要去打仗,而不是準備好走入家庭,但他們的確是家族中的模範夫妻,也給了我們所有人有家可歸的感覺。八歲的時候我的爸媽離婚,貝里格成了我的避風港。
賽爾吉是貝里格一間中學的校長,也是一名二戰老兵,事實上他還在一九四三年那場慘烈的庫爾斯克之戰(Battle of Kursk)裡失去了一條腿。退休後的他照顧花草,也照顧他的一票曾孫。離婚後的父親自我身邊缺席之後,賽爾吉挑起了為人父的責任。講話輕聲細語,態度不慍不火的他鮮少大聲說話或失去耐性,但這並不妨礙他的力量與堅毅。記憶中他唯一一次對我發脾氣,是因為我在他的圖書館裡囫圇吞棗讀了大部頭的列寧手筆,判定想侮辱我六歲的小表親,最髒的髒話就是布爾喬亞(資產階級)。「我們家沒有誰是布爾喬亞!這個字不好聽!」賽爾吉無意間聽到我這麼說的時候非常生氣。他從十來歲就忠誠地擁抱共產主義運動,一路上堅定不移。當然我想用「布爾喬亞」罵弟弟妹妹,要的就是這個字眼象徵的污辱性,但我沒有頂嘴,而他開始思考自己是不是不該放任一個十二歲的小孩自己列書單。聽說這件事的阿絲雅倒是笑得很開懷。
阿絲雅曾跟賽爾吉在同一所學校服務,但等我出生的時候她早已從教職退休,改把熱情投入她的果園,為此蒐集了各式各樣的花卉與果樹。一直有著實業家細胞的她把握住機會,政府一開放民間小規模經商後,她就在波爾塔瓦的中央市場做起鮮花跟水果的生意。在貝里格被稱為「市區」的波爾塔瓦是個安靜的鄉下地方,有著新古典主義造形的白色建築、薄荷綠的教堂,還有尼古萊.果戈里(Nikolai Gogol,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文學家)這名波爾塔瓦子弟的紀念碑。從貝里格搭巴士到波爾塔瓦要十五分鐘,而阿絲雅天天都去,只有星期一例外,因為星期一波爾塔瓦的市場休市。阿絲雅把她的積蓄都投資在金子上,所以當蘇聯解體經濟一道崩潰時,她跟她的身家都毫髮無傷。她靠著櫻桃園讓我們有得吃,有得穿,也讓我撐過了一九九○年代初期的混亂。阿絲雅不覺得被叫布爾喬亞有什麼問題。
不同於我拘謹古板的外曾祖父,阿絲雅生得一副伶牙俐齒,開玩笑的尺度也很大。期望誰用如珠妙語讓人跌破眼鏡或一頭霧水,靠她就對了。某天,年紀已經大到足以在學校喜歡上男同學的我突然納悶起一件事,那就是阿絲雅跟賽爾吉是怎麼結的緣。那天下午,陽光通過狹窄有著直櫺的窗戶,將琥珀色的光束披在厚重的橡木桌椅跟一組茶具上。在市場忙了一天的阿絲雅正在喘口氣,畢竟工作日她早上四點就醒了。
「阿嬤,妳為什麼會嫁給阿公啊?」我對阿絲雅說俄語,她回答則用烏克蘭語,這在我們這種通婚的蘇聯家庭中是很常見的溝通模式。
「為什麼啊?因為我是笨蛋啊,」她說,顯然沒有意識到她的回答我聽不懂。我預期的答案是吉他小夜曲之類的追求,畢竟我看的電影跟書本都是這類情節。
「我是個美人,」她補了一句,邊說邊用雙手比劃她年輕時身材多麼婀娜多姿。這我相信,因為七十幾快八十的阿絲雅還是個很耀眼的女性,高䠷、氣場十足,還有著魯本斯筆下的女性曲線。
「妳外曾祖父愛上我了。」這句我也相信,因為都老夫老妻了賽爾吉依舊對她百依百順。他二戰時是坦克師,但在家還是阿絲雅發號施令,叫他打哪裡就打哪裡。故事說到這,我們祖孫安靜到可以聽到鴿子的翅膀在屋簷下拍動。
「他有一張配給卡,」她說。賽爾吉這時剛好提著一籃櫻桃走了進來。「阿絲雅,妳到底在亂說什麼!」他一邊說一邊臉紅得不輸櫻桃。阿絲雅用她頑皮的藍眼抬頭瞅了一眼,然後爆出了銀鈴般的笑聲,不用說也知道賽爾吉聽了還是會小鹿亂撞。他搖了搖頭,無奈走出房間。
當時我並不明白阿絲雅的故事代表什麼。要說她的婚姻是建立在冷冽、將本求利的計算,似乎不太可能。賽爾吉只要一看到她,深鎖的眉頭就會鬆開,氣色一亮。「願妳有天能找到愛妳像賽爾吉愛阿絲雅的人,」我母親會說,好像那是一件有點不可能的事情一樣。我兩位「阿祖」的婚姻維持了一甲子,我母親才撐了八年。但外曾祖父母是在村中當教員的時候相識,然後一九三二年飢荒爆發。在那段歲月中,配給卡是人能活下去的最大利器,賽爾吉身為資深教師就握著一張。他迷戀阿絲雅,當他求婚時,她也接受了。她並沒有假裝自己是為了愛而嫁給他。
阿絲雅的故事像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精妙的情節內含著其他的寓言,只有覺醒的人才看得見。我太年輕,太篤信蘇聯的大內宣聽不出阿絲雅的言外之意。在八○與九○年代的學校裡,我們受的教育是農工是社會的基礎,是共產黨統治下主要的受益者,蘇聯政府「從邪惡地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人,他們不會讓這一批人活活餓死。史達林主義在六○年代遭到赫魯雪夫的否定,但列寧仍舊是好人來著。學校制服上有一枚少年先鋒隊的星星,而那顆星星印有這名布爾什維克革命領袖的側影。穿著這制服,我滿心期待自己戴上紅領巾的一天早日來臨。列寧本人說過,「工人與農民的智力正在成長,他們奮鬥要推翻布爾喬亞的力道也愈來愈強。」我是在賽爾吉的一本書裡讀到這些東西。要到很久以後長大了,我才慢慢拼湊出這些拼圖。
阿絲雅是我們這個家的核心,每次阿姨一家來貝里格住,我都很開心,因為代表我得讓出房間去跟阿絲雅睡在一起。外曾祖父母是分床睡的—賽爾吉的床是一張窄窄的斯巴達式行軍床,阿絲雅的則是一張巨大的精美彈簧床,上面還鋪有刺繡的枕頭跟色彩繽紛的棉被。我蜷曲在她的身側,一邊是她柔軟的肚子,一邊是刮人的土庫曼掛毯。賽爾吉經常會半夜起來—他被截肢的腿讓他不舒服,隱隱作痛的痙攣會從那兒傳到全身。到了早上,他會有裝上義肢的一整套儀式。我看著他用一層層法蘭絨裹住淺粉色的殘肢,入迷的程度不輸我看著阿絲雅的假牙飄在裝水的玻璃杯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用鐮刀切穿了這個家,留下了各種傷疤,但對我來講那都是某種日常。
「跟我說個妳以前的故事,」一旦我聽到賽爾吉的呼吸變得均勻緩和,我就會這樣跟阿絲雅說起悄悄話。她鮮少在他面前講她的故事。但這些謎樣的故事讓我目眩神迷,在我的記憶裡縈繞不去,於是我會催著阿絲雅跟我多說兩句。
「都是些老女人的廢話,我的故事就是這樣。別讓妳的腦袋瓜裝這些沒用的東西。過去的事就過去了。」阿絲雅會這麼堵我的嘴,然後一邊闔上她的書,一邊把刺鼻的藥膏抹在她被玫瑰刺刮到的手上。但也有些時候,她會順著我開始說。
在我十五歲跟母親、繼父與弟弟移居到芝加哥之後沒幾年,阿絲雅與賽爾吉就過世了。在美國的那二十年,我只回過貝里格兩次,而且這兩次都讓我非常沮喪,因為他們不在了,看什麼都讓我觸景傷情。我看著雜草叢生的花圃跟結在阿絲雅農具上的蛛網,賽爾吉的義肢立在屋裡空虛的行軍床邊,在招灰塵的家具間顯得分外光亮。由於外婆瓦倫提娜當時還住在基輔,只有夏天才會回去貝里格,所以貝里格的屋子跟果園都有點荒廢。母親跟阿姨會固定每年回去,因為他們實在割捨不下貝里格這個「生命紀念品」。但對我而言,缺了阿絲雅與賽爾吉的貝里格已經沒有意義。我將之封印在記憶的琥珀中,從此不再提起。阿絲雅教過我過去的就過去了,我想聽她的話。我變成了遺忘的專家,任何不舒服或會讓我痛苦的事情,都會被我掃到名為「過往」的檔案夾裡。
如今,我必須要回到那裡,因為外婆瓦倫提娜已經賣掉了她在基輔的公寓,在貝里格住了下來。
編輯推薦
【編輯推薦】一針一線繡出來的烏克蘭家族史
◎文/陳雨柔(編輯)
作者維多利亞.貝林姆決議在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歷史時刻,自比利時返回烏克蘭。以她曾祖父的日記為線索,著手調查一位在蘇俄統治時期被當時的祕密警察單位「公雞之家」帶走,從此了無聲息的家族成員。
時隔近一百年前消失的遠親,家族間政治立場的差異,與在世親人面對歷史的漠然,都使得這趟回家的路挫折連連。本書以一個家族的祕密,輻射出一個帝國邊陲之地的複雜及難處。也寫出力欲探究真相之人,如何在猶如迷宮的家族記憶與糾纏難解的政治前駐足,以耐性與時間克服迷惘與頓挫,一一勾勒出每位家族成員在這段歷史之中不同的位置與觀點。在歷史的真相前謙卑,並在歧異處尋求共通的情感及記憶。
更多編輯推薦收錄在城邦讀饗報,立即訂閱!GO
作者資料
維多利亞‧貝林姆 Victoria Belim
出生於烏克蘭,並於十五歲移民至芝加哥,現居比利時布魯塞爾。是記者、譯者,也是一位研究氣味的專家。曾為《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Elle》與《美麗佳人》(Marie Claire)等雜誌撰稿。注意事項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